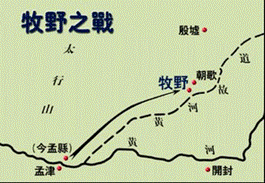���e����
|
�Q��(�U) |
|
�j�����q ���}_ http://www.jackwts.tw/ |
|
�j �D �� �� |
�� �� �� �� |
||||||||||||||
|
��Ū�g�� �k�ߥR�� ����y�� �H���Ѱ� |
n1 �Ĥ������C_ ��
�l��G�u�M�Ӧn�ۥΡA��Ӧn�۱M�F�ͥG�����@�A�ϥj��(136/260)�D�F�p���̡A烖�Ψ䨭�̤]�C�v�O�G�~�W��ź�A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C�꦳�D�A�䨥���H���F��L�D�A���q���H�e�C�֤�G�u�J���B���A�H�O�䨭�C�v�䦹���P�I�]�ԫ����`�A�Y�����ĤG�Q�K���Ĥ@�`�A�[�ĤG�Q�C���ĤC�`�^ �i�Ÿt�դl���q�j 1. ���D�̱N�H�P�ΡA�w�̥�����ơA�D�Žױo���A���H���D�]�C�D�b�ѤU�A�J��ƪ��A�H�ҬI�Ӭҩy�A�h�D�]�C�G�g�l���H�X�B���ޡA���H�a�d��ӡG�G�I�Q�]�A��^�I�Q�ӵL�ҥ[�F�G�h��]�A��^�h��ӵL�Ҵ�F�G�i�f�]�A��^�i�f�ӵL���g�F�G�w���]�A��^�w��(137/260)�ӵL�Ҽ~�C�G���H�J�Ӧw�A�H�J�ӱo�F���]�Ҳ���ߡA���]�쥢��ӡF��Ҧu�̰��A�G�����٤��F��ҥѪ̥��A�G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F�Ѩ�P�O�b���A�ٹ���A�s�i���`�]�C�G�����Ӧ�A���Ʃ�~���F�D���u�C�۱o�A�L�����o�I�p�O�l������D�A�ӯ��D�̡C 1.1 �\�D�̦ܥ����A���L�I�Q�h�⤧�i���B�i�f�w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]�F�u��ҦP�A�h�ߤ��G�B�Ӥ��ɡF�v��Ҳ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~�N�J�C���}�I�Q�Ӳ���ߪ̡A�I�Q�����Ф��A�D�D�]�F���h��ө���Ӫ̡A�h�⤧���Ф��A�D�D�]�F�i�f�Ӿk�䤺�̡A�i�f�����Ф��A�D�D�]�F�w���өĨ��̡A�w��(138/260)�����Ф��A�D�D�]�F�ߤ��Ҧs�w���A���D�Ф��C�G�檫�ӫ�N�ۤߥ��A���檫�H�P�䪾�A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ҧЪ̡F���ӧФ��A�ʱN�O���H�D�N�O���H�G���D�̦۫H��u�A��D�̦ۿ��ҥѡF���b��~�A�D�����䤺�F���g�l���D�]�C 1.2 �g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@�A�H�D�����A�G�X�~�����A�W�U����A���D�O�̡F�ӹD���A�U����y�A�ܤ��ܱ`�A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L���Ӥ���F���]�W��Ӧ۰��A���]�U��Ӧۨ��A�G�b�W������U�A�b�U������W�F���ߤ��ʡA���v�ӵL�D��H�A�G�W����ѡA�U���פH�F���u��q�D���b�B�u�D�����B��D���h�̤]�C�G�g�l�Q�D(139/260)�ӿ�I�Q�A���D�ӻ��h��F�w��ҹJ�A�H�S��R�F�~��ҩy�A�H����ѡF�G��~���S�R�A�ӵL�k�]�C 1.3 �p�H���M�A�����O�v�A�G�h�D�F�D�����o�A�G��c�C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ҩw�A�ӱ��H�H�Ӥ��F�����Ѥ��ҨϡA�ӱ��H�O�f���F�S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w�A�H����ѩR�F�ӿ״��O����f��H�o�֡A�E�ܩ����Ҵc�A�ƨƬҫD�F���ҿצ��I���ƪ̤]�C�\�o���̼ơA�a�\�̩R�A�p���b�ѡA���P���q�C�e��c�ӱo���A�O�����o�A�H�I�D�]�F��c�ӵL�ұo�A�O�Ѳz���M�C���D�̤D�බ�����R�F�p�H�����D�B�����ѩR�A�D�����ƬO�ϡA����ҥH�פv�Ӯ`�H�]�C 1.4 �G�I�Q(140/260)�D���i�D�A�g�l�D���h��A���b���ҨD�����D�Ӥw�C�e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ѡA�H�w��ҹJ�F�_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H�s��R�F�h�I�Q���D�ۦܡA�h�⤣�h�����F�Z�ݦ��I�H���䤣�i���A�ӧƾ����Ʃ�U�@�v�H�G�m�ѡn��G�u�ۨD�h�֡v�C���H��֡A�c�H�{�o�F�e�ӥG���A�Ӫ�v�H�ɡA�h�g�l���D�]�C 1.5 �G�g�l���b�D�v�A���D��H�A�礣�D��ѡC�Ө�o�]�A�D�H�һP�F�䥢�]�A�D�H�ҹܡF�Ҧۤv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G�ण���ѡA���ש�H�C�g�����D�A�䤣�����[�A�D���[���S�A���ϨD�Ѩ��A���Y�g�l����]�C���ӥ��A�~�骽�A���}�ڼf�T�A�ӫᨥ���A���g���}�̡C�D�v(141/260)�w�ɡA�Ϩ��H�ۡA���褣�סA�ӵ��w��i�A�ӫᨥ�o�A���g�l���D���]�A�䬰�D�Z���v�H�O���p�p�H�����I�]�v�H 2. �g�l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A�B�@�b���F���h�ɤv�ӵL�D��H�A���h�ߤH�ӵL�l��v�A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]�C���@���áA���D�Q�C�g�l�H�v�A�b�쬰���F�p�H�H�áA�o�Ӭ��y�F�Ϥ��h�f�Ӥ��y�C�G�B�L�D�A�Ӱ��x�p�S�A���p�H���o�Ӥ]�C�ӧg�l�~���S�R�A�����u�L�滹���A�Q�B���v�A�H���䨭�Ӽ֨�D�F�Y���̶����A���D���ΡA�h���u�۽t�Ҫ�(��10)�A�H�T�䨭�v�F�Τ��@�M�h�A���w�I�W�F�h����L�w�A(142/260)�H�ѩ�ơF�ҭI�D�]�C 2.1 �G�b�v�@�A�T�Q�w�h�F�ӳB�îɡA���ֹD�C�S�R�̥��~���A���䭼�ɦӬ��i�h�]�F�i�i�h�i�A�i�h�h�h�A�ۤ��ީ�ơA�礣�H��D�A���ҿש��]�C�e������i�h���t�A�k���X�B�A���_�I���ӳ{�a�o�F�ۨӽ�̤��J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A�Ҧ]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G�媾�]���^���h�A�����D�ΦӦ�ױ���F�e�M���ҡA�פ��y�H�D�ΦӦ��m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B�@�̭n�̤]�C�~�W��̡A�T�����H�۪��A�Ӧb�U��̡A���S�H�۳B�A�H�ɨ�v�B�w����A�ӫ�K��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̭n�̡C 2.2 ���]�M���۷M�A�ӱ��ۨ��F�⤣�۽�A�ӧƦ۱M�F�B�å@�Ӧk(143/260)�D�ΡA�H�j�D�ӹ��Ʀ��I�F�p���H�̡A���K�G�H�G�~�W��ź�A�ӫ�o���F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A�ӫᵽ�ơF�꦳�D�A�h�M���H�J�ɡF��L�D�A�h�q���H�ۻN�F�ҵM��i�פ������A�ӧJ�O�䨭�̻P�C�G�g�l�u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椤�e����F���D�O�̡A���w�O�̡F�s�i�ٹ�A�J�v�_§�F�H�ɨ�ʡB�w��R�A�L�L�ҨD�]�F���h�g�l���D�o�C
�i�z�t�l�����z�j_ (���z�Ĥ����j��) 1.
�u���e���D�v�|�r�A�����й�Τ��~�A��H��椧�ơA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z�Ӥw�C�H�ͩ�Ѧa���A�L�ɵL��A�����Ҭ��A���Ҭ��ӫᦳ�Ҧ��C�M���Ҭ��̡A�����Ҥ����F�h�䤣�����A�ӴN������A�ӫ�Ҭ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T�H�H�ҦP�̤]�C�u�h�N�v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h�A�O�פ��D�C�p�D���M�A���ѩή|�A�Φi���I�A�ɳ���e�A�N�־A�C�H�G�D�̡A�H(145/260)���ҥѡA�S�Ȧ�̤��Ҧۤ]�C�D�H�@�ӹF�A���H�@�Ө�F�����Ѫ[���ӯ���Ҧܤ��a�A�Y�����Ѳ��D�ӯন��ҧӤ��\�F���ܹD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]�C�h�̡A���e�]�C���e�̡A�ܱ������A�ܤ��ӵL�Ұ��A�ܩ��ӵL�ҩ_�A�ܤ@�ӵL�Ҫ[�A�G�Ѥ��L���F�]�C 1.1 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H�H�ƦӨ��C�D�����M�̡A���ݰݩ�H�B�ԩ]�F�H�ɦӦb�j�A���ݨD����~�]�F�H�B�ӳ{�j�A���ݳV���]�C�G�j���Ѧa��뤧�y�A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~���סF���D�D���Ҧb�A����D���e���D�Ҧs�]�C�Ѥ��h�A�A�I���h�áF�u���h�y�A�����h�b�F�P���h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F���H��(146/260)���i���ئӧѤ��̤]�C 1.2 �H�ͦӥH�����B�֩�ơA�L���M��_�A�@�]�C���o�Ӳz�A�Ʊo�өy�A�٤��e���D�A�N��H�P���H�G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H�H�z�U���A�y�U�ƪ̤]�F�����Ҭ��t�娥�A�Ӹt�妨��O�F�����ɬ��ѹD���A�ӤѹD�ɩ�O�C�G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q�W�U���~�̤]�F�]�|��ʡA�z���H�v�A�L���w�y�C���t�H�ҥH�߫h�A�ӱ������Ъ̤]�C 2. �M�D���b�H�A�H�����Ѥ��A�ӭI�D�H��A�D�D�����F�D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]�C�H�����D�A�h����z�U���B�y�U�Ƥ��h�A�Ӫ����o��ҡA�Ƥ��o��y�A�h�èo�C�G(147/260)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@���ä]�C�J�����D�A�h�L�Ѧ�D�F�D���ۦ�A�D�@���_���D�C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D�]�F�H����D�A�D�D���A�ӤH����ͥͤ��ǡA�h�ͤ��O�F���O��͡A�w�H�B��Ѧa���H���ä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۫O����o�I�O�ҥѩ�L�H���D�B��D�աC 2.1 �G�����D�A�h�ӤH���ۥ��F����D�A�h�H�����@�O�C�D���B��A�@���j�v�A���W���@�H����i�w�]�C�H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D�A�H�ҥ��D�A�ѤU�@�áA�L�H�O��͡A�S���W�@�H�����]�C�G���D�̡A���H�ҩ��D�F��D�̡A���ѤU�ү��D�C�ӤѤU���H�A�J�����[�o�A�D������ı�A�H�ޤ��_��D�A�h�D�ñ�A(148/260)��L�����椧�ɡA�G�����N�@�v����i�l�]�C�����Х��l��ǡA�Ӭ��H�����v�̤]�C 3.
�\�D���b�Ѧa���A���U���U�ƩҲשl�A�H�ͥH���A�D�D�h�ѡA�L��M�A�D���D���v�C�G�D�̡A���v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]�A���P�H���@�ͦ@�|�A�ٹD�h����ҥH�ͨ|���ǡC�G�t�H���D�A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̤]�F����\�A�h��Ѧa�B�|�U���F����ġA�h��ΰ_�~���Ƥ]�C�e���F��ΡA�h���K�~���ϡF�e���q�䷥�A�h���K�N��եءC�G�D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e�F�D����A���e�F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ɹD�]�C 3.1 �Ѧa���j�A���ͩA�먣��ʡF���Ϊ�(149/260)�X��L�ΡA�U���̩l��@��F�ҹD���ҥ]�A���e���ҳe�]�C�����ιD�A�L�����q�A���t�H���w�A�q���C�D���ҥΡA�����A�ɩ������A�L�Ƥ����A���t�H���w�A����U���C�ҩ��ҹD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�~���e�A�Ӽw�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]�C 3.2 ��
�Ҥl��G�u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~�C(��11)�v���H�ɤv�A�h���ߡF���H�Ϊ��A�h�~�q�F���~�ұq�A�H���P���F���D���ҩ���A�Ӹt�H���Ҧ��w�A�ѤU���Ҧ��v�]�C�m�j�ǡn���СA�����P�A����v���A�Y���q�]�C���D��D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Ӫ����ܡA���l�\�����۪���]�C���ߤΤH�A�h�w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Ϊ��A�h�ʤ��ɡF�����w��(150/260)�ܩv�]�C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Y�e���l�סA�Z�@���H���A�۷N���ߡA�ҬO�D�]�F�@���H�~�A���a�v�ꥭ�ѤU�A�ҬO�D�]�C�G���e���D�L�ҬI�Ӥ��y�A�n�b�H������B�椧�աC 4. �G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A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w�F���ܦӫ���ܡA�w�ߦӫ�D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Ф����]�C�G��D�̥��ݾǥH�P�䪾�]�A���D��w�~���U�ۤ��ơA�H����w�]�F�Ӥ��e���СA�Y�e�O�l�סA�H�����h�j�C�G�����ӤW�ǰݤ��q�A�ӱ��έ۱`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F�ϤH�ѩҾǩҪ��Ө���Ҧ�A�椧�����Ӽw�H�ߡA�h�i�D�o�C�\�D��(151/260)�b�H���ʡA�ʤ��Ҩ����w�A�ʵL�i�W�A�ӹJ���h�W�A�G�Ѽw���j�C�w�̩�v��H�A���ұo�]�F�]�Ʀӫᨣ�A�G�w���̨ƦӦ��C�w���ҩl�A���Ѿܵ��ӨӡA�G�̪��ӫ�ߡF���檫�P���A���w����]�C 4.1 �m���e�n���ǡA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ӶQ�b�u�F����A�T���s�i�A�ӶQ�b��C�D�u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F�D��h��i���T�A���N�ɤ��F�G�i�l���A��i���ӡA�l��ܩ�D�C�Ѥ�Τ��ơB�@���@�ʤ��L�A�Ҧ��Ҫ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Ҧu�B���Ҧ��~�A�ӫ�q�T�̤@���A�O�צ��w�C�G�t�H���СA�d���U�y�A��w�F�w���h�D�ۦb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]�A�B�D���w�L�i���]�C(152/260)�G�H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Y�a�x�����d�l�S�̤��ݡA�����D��Ҩ����w�j�F�����p�g�ڤ]�B�p�B�ͤ]�B�p�m�Ҿ[�ؤ]�A�ҨD��Ҩ����w�F�����Ӥ@��]�B�ѤU�]�A�ҨD��Ҩ����w�F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Ӧܩ]�A��ҨD��Ҩ����w�C�w�����o�A�O�Y�ʤ��ҺɡB�������ҦܡB���q§�����ҬI�B����(��)���H���Ҧ��A�ѬO�ұ��L���y�A�ҹJ�L����A�O�h�פ��D�o�C�G�D�̡A�w���Ҧ��F�Ӽw�̡A�����ҩ��B�椧�Ҩ��]�F�٬O�h�D�D�o�C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����w�̡A��q�T�p�O�o�C 5. �ҹD�H�w���A�w�H���ۡF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w���]�ơF��(153/260)�Ѧa���j�h�]�C�G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��N�x���δM�`���ơC�@���]�A�ӵۨ�D�F�@�Ƥ]�A�Ө���w�F�ӫ�פ�����w�B���D�̡C�٪��A���~�N���D�G�H�٨ơA�ƥ~�N���w�G�H���T���ͥȲz�̩Ҭ��A�Ӥ������ǡF�����q�ͩ�ީ��A��۩�峹�A����ɩ�D�w�v�H�G���e���СA�����A�D�ר�L�z�F����j�ӵL���A��Ӥ���A���ɤH���Ϥ��~�A�Ӥ���ϥ@�v���A�H�B���U�o��Ҥ]�C�G���e���D�H��B���l�A�H�H�B�Ƭ����A�H�w���x�F�H�ߤv�ߤH�B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F�l���P�ۥ��H���䨭�A�ש�v���H���ΤѤU�C�G���̨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A(154/260)�Ϥ��o�Ҥ]�F�q�̨��˿˴L��A�Ѫ�ӻ��A�����ҩy�]�C 5.1 ���q���H���D�A���H�ͤ��ҫO�A�Ӥ��i���إ����̤]�C�G����i�A���b�@�ߡA�H�ɨ�ʡA�ϩʹD���h�]�F���Ǧ�A���b�@�w�A�H����D�A�ϹD�w���Ω�H���]�C�ѬO�ӶԶԲj�B�F�F�j�A�H�D�䤣�G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ҡC���G�h��i���өʨ��A�����h�Ǧ�q�ӹD�w�s�A�G�̤��~���Ƥ]�ӦP�ܡA���ܫh�~�ܡA�~�ܫh���ܡC�~�ܪ̡A�����w�]�F���ܪ̡A��ܵ��]�C�J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_���ܵ��A���ҿD�����o�A�t�H���ҦW�A���H���ҤΤ]�C�M�D��l�A�T���۲Ӧ��δM�`���Ƥ]�A�����B�@(155/260)���D�]�A�@�����w�B�@�a���q�A���Ӧܩ�ѤU�H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y�]�C�G�Ǫ̥����D�ƪ������e�j�A�٨ƪ��L�ਣ�䤤�e�]�C 6. �O�G�� 6.1 �G�D�����`�̡B���B�@�̡B���˿˪̡B�������̡B���R���̡A�Ӳ�����۲�C�\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D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D�N�O��H�߬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A�ߤ������A�w(156/260)�N�O���H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N�����ۡA���N�O���H�G�w�ۤv�l�A��D�ۨ��l�C�Z�@�����ҳB�A�ΥΩ��áA�κa�ΰd�A�Φb�W��Φb�U��A�Ω~����Ω~�i�f�F�λP�a�H�λP�˱ڡA�λP��H�λP�����F�L�����̩y���D�A�ܥ����w�A�H���I���F�O�h�g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@�]�C�䦳�J�ð�B�{�å@�A�A�K���ڡB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b�H�Y�L�Ҩ̴`�A�N���䬰�D���w�C�ӧg�l�����]�A����u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ܵ��өT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ߡA���H�ҧx��ӡF�D���H�J�Ӧw�A������D�w�C�G�a���D�B�F���w�A�~�W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D�A�~�U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D�F�B�v���i�k���D�A�B��(157/260)���۫O���D�F���Z�礧���B�V�~���s�A�����H�ʨ�ҾޡB���Ҧu�A�ӯ�۵��ݵ��A�H���䩾���A���h�g�l�����e�]�C�G�g�l�̡A�H�D�w���W�A�H�ӵL�w�A�h�L�H���g�l�C���j�t�H���ҭ��b�w�A�Ӥ��e���Щҥ��A��ټw���Ѥ]�C 7. �ҹD����A���H�Ҧ��w�F�H�Ҧ���w�A�w��L���Q�A�G��W�w���w�C�M�@�����u(��12)�A���w�̤֡A�w�D�Q�o�F�w�Q�ӹD��A�@�D�áC�H�S�O�]�A�H���w�ӥ��D�A�E�ܩ�áA�H���w�Ӥ����D�A�h�ܩ�v�F�v�ä����A�b�G�|�w�P�_�A�D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]�C�G�����w�A�H�v���ѤU(158/260)�̡A���D�^�w�����A�ӤH�v���Ӭҩ���w�A�h�@��L���w�̨o�C�H�L���w�A�ѤU�����v�̥G�H�G�v�@�̡A�H�H�v�H�A��䤣�w�Ӭ��w�աA���ݦh�N�]�C 7.1 �u�H�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S�H�^(��13)�v�A�֤���]�F�e����͡A�ӱo��ҡA�൯�S�����]�A�|�����w�̥G�H�G���w�̡A�g�l�˿˦ӽ��A�p�H�ּ֦ӧQ�Q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ҥH���h��w�A�ӥ@�êv�o�C�G�|�w�̡A�Q�ɤH���ʦӱo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P�өʦP�]�F�e�ɨ�ʡA�h�A��ͨo�C�g�l�H�D�A�p�H�H�Q�A�D���ұo�A�g�l���Ҧw�A�Q���Ҧb�A�p�H�����k�A������ߥH����w�A�@�H�����n�w�o�C�G�g�l�����D�]�A(159/260)���L�w����A�ϤH�IJj�A�w���b���A�p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A�L���q�Ӷ����C�G�w�b�D�Ѥv�A�v�����ɡA�L�H�ɤH�A�v�����w�A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C�G�g�l���۳d�]�C 7.2 �@���ä]�A�����`�]�A���t�H�H�w�Ф��A�Ҷê̪v�A�Ӯ`�̰��A�����ܱ��C�G��Ϥ��@�A�ѤU�P���A�D���ʮ��]�A��ϬL��w�H�Х��]�C�Ϥ��A�h�L�w�̦b��A�����o��СA�۲v�ӮĨ䤣�w�A�h�ѤU�ҥ��w�o�C������@�A�ѤU�h�ɡA�D���ʮ��]�A����ܨ�ɥH�v���]�C�G���e���СA�H�w�Ф]�A�H�`�ЦӬҤ��e�A�h�ѤU�L���w�o�C�G�t�H�H���w��ѤU�A�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�@����A�D���D�]�C�D��(160/260)�A�U���ͦ����h�]�F���@����h�A�h���o�ͦ��F�����o�ͦ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p���o�ͦ��̥B���h�G�H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Ф��ҫ�]�C 7.3 �H���B�@�A�Y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A�Ӥ@�v���ͦ��A�ټw�����A�O���w���v�]�C���w���v�A�ӤH���Ҧ��A�G�g�l���ɦb�v�A�ӥ@�|�Q��w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ۨ��l�]�C�H�T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H�ͦ��A�����ͦ��A�Y�^���ͦ��A�����w�A�Y�^���w�A�����ҺɡA�Y�^���ҺɡC�G�g�l���w�Ω�ѤU�̡A�S�䨭���w�]�C�G�D�L�H�ڡA���D�䦨�F�w�L�j�p�A���D����A�ɨ�@�h�ҺɡA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e�W�U�̤]�C 8.
(161/260)�`���A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��H�ͤ��j�h�A���ݨ䬰�H�P���]�F�e���ѬO�A�h����ͥͤ��ǡA�����崼�A��Q�H�G�崼�L���A�S�M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Τ]�C�@���Q���崼�A�礣�w���M���v�A�ҶQ�b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ұw�b���D���e���СC�G���e�̡A�ѤH���D�Ҧ@�Ѫ̤]�A�H���P�H���ͦ��A�Ѧa�P�̦��и��A�T���i���إ����̤]�C�@���g�l�A�|��O�椧�v�C
�i�ȸt�s�l���z�j_(���z�Ĥ����j��) 1.
(164/260)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b�H�H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B�ɥG���q�A�h���e���D��F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椯�q�A�h���e���D��C�����H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Ӵn�@�����v�A�Y�]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e���D�Ӧ椧�]�C�䤣���̡A�D�Ҥ����]�A���̹L���]�F�D�H��M�]�A�M�̤��Τ]�C����̡A�D�Ҥ���]�A��̹L���]�F�D�H�䤣�v�]�A���v�̤��Τ]�C�\�����Q�A�Q�H���e�Ӵ��F�M�D�f�A�f�䤣�Τ��e�ӷM�]�F�夣���_�A�����e�ӫ��F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Τ��e�Ӥ��v�]�C��H�����H 1.1 �H���ٽ崼�]�A���䪾��ӤH�]�F����ӤH�A����ϤH�Q��w�A�M�̿ध�H���A���v��(165/260)�ध�H��A���ҿ崼�̨o�C�e����w�A�Ӥ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O�L�q��H�A�䪾�ण�����]�F�Ψ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ӳx��~�O�H�b�@�ɥ��A�H���o��q�A�B�Q��`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C�G���A�G���e�A�ӫᬰ�഼���F�L�G���e�A�����P��A���D�ҭ��F�ӹD���ҥH����̡A�Y�ѬO���j�C 1.2 �@���M���v�̡A�����ध���e�H�]�F���ण�e�A�D�f�]�A�����ӤΤ��A�H�D�䤤�e�A�h�M���v�i�i��崼�o�C�����䪾�ण�e�A�Ӥ��D�䤤�e�A�h�۲ש�M���v�F�ש�M���v�Ӥ��Τ��e�A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Y�i���j�C�G�D������A�b�त�e�A�D���M(166/260)�夣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Ӵ��M�夣�v���त�e�A�h�L�L���ΡA�ӹ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T���ݱФ����\�C���䴼��L���A�M���v���ΡA�Ҥ��o���e�A�ӹD���A�D��ұХH�����]�C 1.3 �Ҥl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еo�]�C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A�ӹ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H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���崼�A����Ҥ��e���D�F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v�A����v���e����F�Ӯ{�ͩ���ɶä����A�B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ҡF�g���۳ߡA���椣�áA�ӥ@��áB����M�F���@�D���ܰI�B�H�D���ܭW�A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ХH���^���C���h
�Ҥl���L�N�A�ө����e���Ф��j���]�C�^�G�ꬰ�еo�աC 1.4 �Ҥ��e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j�ä����A(167/260)�H����Ҵ`�A�Ӭ۲v���áA�����\(��������)�̻����]�C�G
�Ҥl�νΩ�СA���H��áA�ө�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Ǥ��͡F�ӫS�R�~�����q�A�Hĵ���I���Ƥ��ߡA�䦮�`�o�C�\���D�J���A�H�ߵL�D�A���大�h�h�Ҩ�_�Ϥ����A�Ӧn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A�H�b�@�z���F�M���v���{�h�Ĩ�ۥΦ۱M���ߡA�Ӭ����Ʀ��I���|�A�H�`���`���F�ҨƩҥ��ܪ̤]�C���F�E(��14)���u�A�P�D���L�A§�֤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A�G�T��h�۫��o���A�H�ɨƤ��D�A�D�n�����Ԥ����A�}���D�B���Q�N�B��§�СB�|�D�W(��15)�A�����H�G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ǥH�s���ӡA���D��W���ߡA����(168/260)�������ɡF�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h�A���U��O���áC�G�O�D�c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ɯơA�B�h��ij�B���ȩb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(��16)�H�F���J�A�ѥ߽�(��17)�Ө���ۡC�\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[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Ӥ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ĥ���(��18)���N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椣�η������_�C�ܾꤧ�ɡA
�Ҥl���СA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̥�Ȩo�C 1.5 �����ɤ]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H���B���˰ӡB��Ĭ�i(��19)�B���]�d(��20)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U�ߪ���A�Ҭ�����A�@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D�A���ꤣ���䨸���A�аI�D���A�ܴ��w���C�}��쥻�A��D����L���B�M���v���ΡA�Ӭҥ��D���ҭP�C�H�Ѵ������A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D�H�����H�䤣��A����D�H�P���H��(169/260)�Ҩ���k�A�S���D���大�L���]�H�\�M���v�̡A���ण�e�A��v���ιD�աA�Ӥ����H�ùD�C�����大�h�A��䪾��ӤH�F�D�Ҭ��_�Ϥ����B���Ԥ���A�H�ùD�Ӫɥ@�F���D���ҥ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��Ƥl�̡A�v�Ҥ~�T���h�B���Ӥ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i�ܡB�榳�i�H�̡F�{�H�۰��۲��A�Ӥ����H���A�D���_�D�䤤�D�A�H���H�ͤ���A���h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פ]�C�e�仡�j��A���ӥH�b�A�ѤU���áA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H�Ө䤣�ܬO�̡A�h���
�Ҥl���e���ЦաC 1.6 �\�Ҥl���D�A������H�A�L���L��A���ޤ��H�A�J�¤����H�A�S�����ѶǡC��@�o�D���̡A��(170/260)�����_�C�g��զӫ���B�[���m�ӫ�H�A�H��Ѥl�����A�ӲХj�t���ǡC�\�ۤl��l��A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̤]�C�G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ܤ��S���F�Ӥ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@�����A�ܹD�̤��Ҧ��G�H�H���ͤ]�A���̩ҥͤ��h�A�H�A��ͦs���ҡA���T��M�ҦP�F�ӥͦs�һݡA�`�H�ɦa�ܾE�A�Ө����Τ��~���A��]�ɦa����F�G���Х��A�ɡA���D���Τ��C 1.7 �ɤ��]�̡A�H�ͤ��j�D�]�C�j�w�D�����A�Ӥ��y��ɡA�h���_���Q��@�A�p�\�椧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̡A�D�����|�A�ӥΤ��h�N����סC���ͤ��ǡA���i���]�A�e�٨�w�N���ǡA�ӱ����j�A�ե��ɯ}(171/260)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䵥���F�Ӫ��ܤ��Ʀh�A���ͭW����Z�F�Ӱ�O���@�A�h�ͦV�U�[�F���ä��L�w�]�C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{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_��H�A�Ӥ��ѻP�ɤ��y�F�H��Ҩ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̡A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̡A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F��D�����̡A�S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F�ѤU�ɯɡA�N��J���H�H�ߤ��i�w�A�w��@���v�v�H 1.8 �G���Ъ̨D��@�A�H�@�@���F�Ӳ��L���A�h���D�䤤�C�G���̡A�D���Ҧۥ͡A�ӥ��ͤ��j�h�]�C�D�䤤�Ӥ����A���Ӥ��_�A�����Ҧw�A�@���Ҫv�A�D����]�A�Y�b�G�O�A�G�v�D���ۤ��e�l�C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D�a�h�H�ܤ��H�A�D�N�s���H�A�ҩy�]�F�D���@�H(172/260)�d�ѨơA�D�űf�ƥH���䤤�]�C�G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��~�ɦa���y�B�ƪ����Q�]�C 2.
�O�G���e���СA���]���M�夣�v�Ӳ��A�L�S���ΡA���A�y�����C�H�����M�夣�v�A�ӫ�~�Ѥ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ӤH�A�Ӥ��A�@���y�A�S�D�D�]�A�p�M���v�~�Ѥ����Y�H�̥G�H�G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H�Ҷ����A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F�Ҧ���͡A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e�F�����`�]�C�G���e�̡A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ҦP�B�U�ƩҲz�A�D����@�v�����]�C�e�q�F�@���A�e���U���A�L���y�̡A���פ��त�e�A���פ����D�B��D�̤]�C�\���e�L�����A�D�L���F�F�����h�y�A���F�h�z(173/260)�F�v�@�w�����h�A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~�G�O�C�Ϥ��j���A�Y�Ѩ����Τ��F����Τ��A�h��ɤ��A�ӯ��D�F�G�ѤU�v�Ӥv���t�A���e���D�|�o�v�I 2.1 �ҤH�P�O�ͤ]�A�Ҧ��Ҧw��ߡB�ҩy��ƪ̡F�e�H�^�ߤ��w�B�Ƥ��y�A���Ӧ椧�A�L�����o�C�G�t�H�椤�e�ӤѤU���e�A��D�ӤѤU�ҹD�F�T�L�p��v�A�Ӥv����w�F�L����H�A�ӤH����D�C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СA�b�D�v�Ӥw�F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]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]�F�D��v���Ҧw�ҩy�A�H���ѤU���Ҧw�ҩy�A�Z�����v�H 2.2 �G�g�l���v�@�A�b�H�H�v�H�A�H�H���h�A�ӧ��H���ҫh�F�S����_�̡A�H�_���h�A(174/260)�����o�_�̥G�H�H�S�v�]�A�v���J�ɡA���L���q�F�_�����h�A�줣�ܲ��F�ФƤ���A���ݤR�Ӫ����o�C�G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��b�D�v���Ҧw�ҩy�F�v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y�̡A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A�Ӥ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e�ɥG�v�A�ӬJ���o�A�J�D�o�A�L���w�B�L���y�o�A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ѤU�S�B�q���A�p�����̫v�H 2.3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A���H�å@�̡A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y�]�A�v���त�D,�G�]�A�s���e���A�J����t�C �Ҥl�A�t�H�]�A��Ҧ�L�����D�A�G�L���w�y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त�D�̡A�H �Ҥl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w�y�̡A�H �Ҥl�뤧�F�h�ѤU�@��
�Ҥl���D�A�ӤѤU�w�o�F�G�v�@�S�v�v�]�C�Ф�(175/260)�Ҧ�A�Y�w���ҵۡF
�Ҥl����w�A�ӫ�I��СA�G�����ѤU�A�L�����o�C 2.4 ���e�H�ɤ����Q�A�Y
�Ҥl�۹D�]�C�^�G�٤����t���ɡA�䲧�G�B�i���i�B�h�U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Ѯɤ����D�뤧�C�g���Ѥl�A��L�ײj�A�H�䤣���ɤ��A�{�a�@�v�����A�פѤU�i�v�N�w�A�Ϫ��˨�ʡA�H�q��СF����Y�H���h��յٯ����]�C 2.5 �H����ʥH���v�A�O�B����F(�{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)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ϪA�A�ӥͽ�w�\�A����ߦw�A�o�G�H�Y�B�@�]�A���ݨ�z�A���D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A�Ϩưf��z�A�H�q�^���ߡA�S�����K�H�����~�A���O�餧�ϱq�A�ӥ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A�w(176/260)��䱹���y�v�H�G�P�H�H�q�v�̡A�״��i�o�A�D�h�D�A���䥢�w�]�C�w�̥ͤ����A���w�ӫ�D�͡C�g�l�v�H�A�����H�w�A�ܥ������Ҧw�ҩy�A�өw��h�F�H�ܤ��ܩ����D�椧�A�G���Ҽֱq�A�ƬҶ��z�A���ݫj�j�����]�C�G��Ϥ��@�A�����c�c�A�U�֨�͡A�ӫ�@�h����A���䥢�ɤ����D�A�ӵL�H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 2.6 �Ҥl���СA���z���e�A�Ө��h�A�H����D�A�ӭ��b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ҥH���t�C�Ӳ��H�h�Ϥ��A�ȫ�v���Ҫ��A�H�_�Ǥ����A�в��Ϥ��ǡA�H�۶ǭz�A�ӭ��b�M�H�A�����@�ä����A�ӹD���ҥѱ�A�G���o�P
�Ҥl�áA�仡�������(177/260)�A��y�o�C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�̳̭n�����A
�մ��ұ¡A�Y���G�r�C���h�ɤv�A���h�ΤH�A�Ѥ��D�H��A�ӱ���ѤU�A�٩������ѡC��
�Ҥl�W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ɤ����Ъ̤]�C 2.7 ������A�D��o�H���ʡB�ƪ������A�ӯ౹�L���y�B�~�L���w�A�G��ɤ������C�d���ӫ�A�e���D�ɤ����q�A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ɤv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A�g�l�ҥH���g�l�A�ҨD�v�աC�D�v�w�ɡA�ӫ���ΤH���A���T�D���ΡA�өʤ��w�]�C�G�ꩾ���H�D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̡A�����Ѩ��A�Y���_��_���q�]�C�H�v�ΤH�A�Ѫ��Ĵ�A���Y���e���ҥH���e�F���ݽѥ~�A�G�����ܩ��F(178/260)���ѽѤH�A�G�椧�ܩy�F�y��v�ӫ�y��H�A�v�Ҥ��@�̡A�h�ŬI��H�A���Y���v���w�]�C 3.
�Ҥl�H���e����߫h�A�ӦW����g�l���D�A���ҷ��ɤ��A�त�e�]�C�@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e�A���s��g�l�A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g�l���D��~�A�P�D�̡ۨA�D��W�u���e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w�A�G
�Ҥl�٤��C�e���ҿ��Q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Ӥ����̡A�Y�� 3.1 �ҧg�l���D�H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h�ɨ�(179/260)�ҩy�A�e�h�ܨ�ҩ��C�G�g�l����A���Ѩ��ӫ�x��H�A�D�Ѥv�ӫ�ΩA���l��ߨ��A�����A�ש�R���C�G�ۮ�P�ۥ��H�Ϊv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�ۧ����˿˥H�ν��֧Q�A���P�䵽�F�ҩl�ߡA������S�A�ɩ�a��A�ݩ�ѤU�F�����L��w�ӵۨ䵽�̤]�C�w�̡A�D���Ҩ��F���̡A�ʤ��Ҧ��F�G�w���ɡA�ӹD�w���B�ʤw���A���Y�F�v�ߤv����C 3.2 �w�ΤѤU�A���ݸU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A���q���D�ɡA�ѤU�H���ҳQ��w�A�L���w���y�A���Y�ߤH�F�H���D�C�G�g�l�̡A���w�̤]�A�F�D�̤]�A��Ѧa�Ө|�U���̤]�F�M��l�]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v(180/260)����i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w���[�|�C�G��@�Ƥ@�����L�A�ӥ��D��Ҧw�ҩy�F�@���@�ʤ����A�ӥ�����Ҧu�Ұ��F���\�b�G�Ǧ椧�O�]�C�G�g�l���w�A�ߩ��δM�`�����A�l�a���S�Ұ�����F�ԩ�e���A�V��e��F�H���ҲߡA�ӨD����F���T�g�l���D���Ҧ۩l�]�C 4.
�@���ҩl�A�b�a�x�A�����Ұ��S�̡F�b�m�ءA�B�;F���F�b��A���W���ݰ�H�F�b�ѤU�A�Ҧ��H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C�H���H�~�A�_�~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ʧ@���F�@���P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Ѥ��D�C�B�@�����A�Ω~�ΥK�A�ιF�Ϊ�F�ҹJ���@(181/260)�A�D�{�����F�@���ư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C�Ө�Ҧ��̤v�A�ҩy�̪��A�Ҧw�̤ߡA�Ҳz�̨ơA�Ҧ]���ӫ᪾���C 4.1 �G�g�l���D�A���D���F���ݥX�K�A�Y�b�@�a�ɥ�M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A�Y�@���]��M�C�G�w�L���A��D�L���F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i���D�F�����ߡA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C���q�ҥH���H�D�]�A�����ҥH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]�A�ҽt�G�ͥͤ��j�h�̡F�e���O�h�A�h�N�L�ұ��⨬�C�G����L���A�M���v���ΡA�Ҧ]���Ҥj�h�A�Ӯ{���a�䴼�]�C 4.2 �Ѥ��ͪ��A�]���ӿw���A�G�H�D����ѹD�F�H���i�G���q�A�ɨ䩾���A�D���ѹD�A�ӱo�����F�e�f���A���Q����СA(182/260)���Ʋz�����ܪ̤]�C�G�~�å@���M�̡A�g�l�]�F�Y�p�H�hۤ�e���o�I��ƧK�̡A���ͥ�d�A�����ҥͤ��D�]�C�G�g�l�H�ߩR�����F�R�̡A���H�Ӧ���ѡF�ѥH�R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c�F�H�H�D�ߩR�A�h�ѱq�H�F�Y�H�H�c�����A�h�R���ɡA���Ѥ��L�ݡA�o�G�H 4.3 �G�ߩR�̥��ۤϡA�m�ѡn�ҿסu�ۧ@�^�A���i���̡v�]�C�G�g�l�ߩR�A���ɨ�ʡC�ʨ���ѡA���ʪ̶��ѡA�G�궶���䥿�C���̤��D�]�A�ѥG���e�A�h�����䥿�A�G�~�w�Ӧ���F���H�~���䤤�A�G���M�F���H���l��w�A�G���I�F���ߩR����A�Ӻɩʤ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
�Ҥl��ˮ���B�ȩ�J�H�B�d��(183/260)�A�ӥ����ʨ䤤�A�D��i�M�S�w�B�i�I�S�i�A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A���H�ߩR�̤]�C�G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D�Ѽw�A���R���D�ѩʡA���ѥ��D���H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F�U���ҳƩ�ڡA�ѤU�ɩ�@�ߡF���D���שl�A�ӧg�l���椧�ҥ�]�C
�i�v�D���t���z�j 1.
�u�ɤ��v���q�A�w���e���F�ӥ����]�崼���L�B�M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ΡA�ҥ����e�F�H�P�D�����椣���A�Ө��g�l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ɤ����СC��Ըg
�Ҥl�B�s�l�����L�l�A�����@�H�S�Υ��F�A��ӽפ��C�\�ɤ����ܺ�q�A�Y�p�@�Ʀb�Q�ҩy�̡A�ܤ��h�_�F�ɩ��G�]�A�����Q�ӨD�䤵�C�b�{�ҩy�̡A���ӫh�_�F�H���ܤ]�A���Ϩ�s�ӧ���¡C���ɤ����D�]�C 1.1 �G�j�D���y�_�̡A�D�_�j�]�A�H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y�]�F�j�D��(186/260)�y���̡A�D�ϥj�]�A�H�����_�y�]�C�өҿשy�̡A�D�x���ơA�H�X��D�F�D�x���ơA�h���}��ΡF�D�X��D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w�C���}��ΡA�h���ӵL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h���Z�Ӧ۶áF�Ҥ����w���v�@�B�ߨ���D�]�C�G�ɤ��̡A���@�Ӥ����A���y�Ӥ��áF���I���A���H�G�ܹD�F�椧�ҩy�A�i���ҧQ�F�ӵL�ҥͩ�ߡA�L�Ү`��ƪ̤]�C 1.2 �s�l��G�u�ͩ��ߡA�`���ơF�o���ơA�`���F�C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ɤ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]�C���]�ߦ��Ұ��A�G�߱`�F���F���]�Ʀ��Ұ��A�G���`�o�y�F���ɤ��ӵL�����]�C�e���H�j�A���@���q�A�h�y(187/260)���̥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Q���̮`�F�����@�A�D�ɤ��]�C�Ưɩ�e�A���v�F�E�����y�H�E�����Q�H�ߤ����F�A�h�b�o�F�Ƥ�����A�h�ըo�F���b�P�աA�����夣�ΡA�箯�ɤ����D�]�C�G�ɤ��̡A���ҩw�ӵL�Ұ��A���ҩy�ӵL�ҥ��A�Q���O�P�A�`���O��(������)�A�D���O�s�A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A���g�l���w�A�L�i�L���i�]�C 1.3 �G�ɤ��̡A���ɤ����A�ɫh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h���w�C�\�Ƥ��ܩy�A�����ܧQ�A�t�H���w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]�ƨ��ΡB�]�����w�A�D���ɤ��A��H�P���v�H���ɤ����i�Q�]�C 2.
(188/260)�N���`�B�@�����A�ۦ���ɤ����D�A���L��L���ΡA�ӫ�X�G�D�C�S�f������A�̭W�ݦn�A�U���ҳߡF�өy�̡̪A�̤D���D�F�y�W�̡A�W�D���D�C�Y�Ϥ��A�̪̬��W�A�W�̬��̡A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A�Ӥ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C�G�B�I�Q�̡A�h�y��I�Q�F�B�h��̡A�h�y��h��F�B�w���̡A�h�y��w���F�B�i�f�̡A�h�y��i�f�F�����Ӧ�ҩy�A�D���D�]�C�Y���Ϥ��A���I�Q�]�Ӧ�h��A���h��]�Ӧ�I�Q�A�O����ҩy�A�Ӥj���G�D�A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e�]�C 2.1 �\�D�̥��G�H���C�B���Ӧ�A�D�l�Y�k�A�g�l�Ү��]�C�B�h�Q�W�A���b�@�z��(189/260)����A�g�l�ҳ̴c�̡C�G�Ӥ��ݵؤh�B�դl�ݤ֥��f(��21)�A�Ҭ��䤣�त�e�F�Ӯ{�B���H�H���A���D���|�F������H�ߥ@�D�̤j�A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ݪ̤]�C�G�g�l���`�B�@�A�Q�त�e�A�I�Q�h��A����Ӧ�A�L�J�Ӥ��۱o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̤]�C�Y�ˤl�����B�L�ͤ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l���G�A�����U�H�Һ١A��D�g�l�ҳ\�C�G��@��l���סA�H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j�l�|�A�����z�o�C 3.
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u�O�H�ƪ����ҩy�Ӧ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@�F��O���G�{���Ӧw�A���]�~���Ӧ��ʩC�G�I�Q����G�I�Q�A�h�⤧��G�h��A�ҥ��^����(190/260)�Ӧۦb�w��A���H�I�Q�h��Ӱʧ^���]�C���n�W�̡A���M�I���_�A�H�W�~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i�T�����I�Q�A�Ӿ���h��A�ۥH���w�h�ѶաA�Ӥ����X�۰��@�F���ߤ��`���I�Q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䶡�A�����B�h��A�S�����اѴI�Q���ۡC�O�H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ӧ^�ʬ����A�䤣�X�D�ƨo�I���h�⤧���w�h��A��D��D�h�⤧��A�䥢��P�F�\�ҥH�߫ફ�A����ۥD���L�]�C 3.1 �G�g�l���D�A�W�ߤ�����v�C���I�Q�]�A�ӤߵL�I�Q���ۡF���h��]�A�ӤߵL�h�⤧�ۡF�I�Q�h��A�۴I�Q�h��A��P�^��z�H�Z�����Ӱʧ^���B���^(191/260)�u�v�H��p�O�A�ӫ���H�ұ��Ӧ۱o�A��L�P�ƪ���椧�{�A���h���e���D�]�C 3.2 �ҤH����i�A�Q����u�A�ӥ��۹�A�H�I�Q�ӥ���h��A�h��ӥ���I�Q�A��ߥ����A��Ӥ��ۤ���A�h��u�w���A�|�y���D�H���L�H�����I�Q�Ӵc�h��A�e�B�@���h�A�h�I�Q�H�D�h��A�b�f�����ۡA�����ध�ơA�����̹L���]�C�S���U���ҡA���h��ӧƴI�Q�A�O�ı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M�̤��Τ]�C�L�̿E��W�A���F���Ϊ̽���Q�A�����R�F�ҥH�~�����䤤�B�ݱ��è�ʪ̡A�|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D�]�A�G�g�l�����j�C(192/260)�g�l����A�L�L���ΡA�@�`���e�A���䨥��L���_�A�ӧӽ줣�i�ޡA�G��W����U�A�ӵS���ĥG�H���B�W�V�G�����A�ӯह�y��U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欰�ܹD�̤]�C 4.
�g�l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Ѩ��A�����ҹJ�A�L�@��~�A�G�L��סA�ӯ�~���C�\�H�ͩRô�ѤѡA�ӧg�l�����ߩR�A������D�Ĥ@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ߩR�A�b�I�Q�T���ন�w�A�ӳh��h����u�D�C�H�R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ͩ�c�]�C�p�H���L���ߡA�ө�����סA�L�Ҥ����A�ҵL�H�ߩR�C�G�]�A�ͦӴI�Q�A�hź���]�h�A�H�ɨ�ѩR�A�Ӥ�(193/260)��`�u�I�Q�F�ͦӳh��A�h�зT��ѡA�H�٨�ѩR�A�Ӥ���ۨD�h�֡F�Ҥ��බ�䥿�]�C�ߩR�̥����䥿�A�H�D����ѡF�e�I�Q�]�A�����w�~�A�w�~���O���ѩR�����F�h��]�A���w�ߨ�D�\�A�D�\���פ��}�N����F�G�I�Q������~�A�h�⤣�x��M�A�ҿɤH�H���Ѫ̡A�ҵ��ߩR�̤]�C�G�g�l�u�D�ߩR�A���_��ѤפH�C 4.1 �R���J�ߡA�ѥ��q���F�R�����ߡA�ѥ��Ф��A��L�q�]�C�G�g�l�B�@���`�A�{�D�Ѥv�A���]�ҹJ�����A�Ӥ���w�A���]�ҹJ���c�A�ӧѦu�D�C�ͦ��I�h�B�ؤԶQ��A�����Ѥv�ۭP���C���(194/260)�����]�ͦ��I�h�B�ؤԶQ��Ӧ��ҳ߫�A��ӥ祼���]�ͦ��I�h�B�ؤԶQ��Ӧ��ҷR���F�G��w�u�䤤�A������ӡB�w���N�B�����ߡA�ӫ��T�����B��R���F�C���L�\̩�A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סF�~�L��סA�G�ѤH�P���F�ҥߩR���\�]�C 4.2 �H���ө�t��A�L�פ~���o���B�ҹJ�e���A�e����ߩR���D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w�C�j�ӻ��Ǥ��h�A����ؤj�~�B�ߤj�W�B���j�\�̡A�Ҥ��J�ߩR�A�{�x��ҹJ�B�~��~���A�Ӥ���۩ޤ]�C���ӤU���A�ͤ��Y�H�A��ҿ��ߩR�A�ʭ��C�t���^�l�A�~�w�n���A�x�~�֤ߡA�e�ۤ��ߩR�A(195/260)�N�Ѧa���j�A��L�Үe��m���F�H�����c�A��L�Ѱ���ݮ��A���h�j���Ӥ��̨o�C�G�H�ͤj�ơA������ߩR�C�ѩR�b�ѡA�ߩR�b�ڡF�t��P��A�T�D�ߩR�L�H����ͤ]�C
5.
�O�G��D���h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ۥߤ��D�A�D�{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@�]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̡A���B�j�H�����s�A�Ө��߯��M�A�L�Ҿ��ǡA�e����D�A�N������U�F�Y�Τ��ѡA�Ӥ��椣�T�A�L�Ҧ��w�C��o��e�̡A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̡A���}�F���J�R�����]�A����L�ҥߦӮ{�x�䴼�A���䤤�ӱ��ۻﰪ�F�G�ʻ��[��(��22)�A��(196/260)���K�@��f�]�C�G�g�l���D�䤤�A���D��L�A�L�S���Τ]�F�L��e�̡A�����Ω��F�L�̡A�����ΩC�G�L���L�q�A�B���`�o�I�H�D�����L�H����A�ӫᬰ��F�ӥ����ܤ����w�A�ӫ�A�D�C�G���e����A�D�Ѫ���F���y��H�h�H���A���w��v�h�H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A�ӫ�H�v�ѱo�F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]�C 5.1 �u���v���@�r�A�b��ߦs�@���A�Ϥ��h���w�F�w�̤ߦ��G���A�h�D���o�C�ߤ������A�ӱw�Ͳj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n�A���D�ߤ��w�աC�ߤ��Ҧw�b�D�A�D�s�h���`�s�A�G�w�F�D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G�A�G�w�͡C�H���ұw�A���b(197/260)���䤤�]�C�ѹD�ܷL�ӵL���ɡA�e�D�ѹD�A�����H�D�F�H�D�R���w�ɡA�ѹD�b�䤤�o�C�G�g�l��G�����A�D�Ѥv�H�S�ѩR�A�ѩR�T�q���o�F�p�H�����ѩR�Ӧh��סA����Ϥv�ӹϹ��ơA�ѩR�����O�A�Өa�e�Ҩ��F���g�l�p�H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b�G��ߩR�_�]�C 5.2 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A�b�v�h�u���A�b�H�h�R���A�ҥH��D�]�C�g�l����D�A���ۥD�j�A������D�A�G�त�ߤ��ʡC�G�ѩR�b�`�A�����e�ѤѩR�A�Ӧ۵e�]�F��G���e�A�L���y�̡A�@�H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@�h�۩T�A���h�ۦs�F�s�B�T�A�G�����ƪ��Ҳ��A�ӯ�D�ƪ��j�F��(198/260)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ӸU��ť�R�A�Y���D�]�C�G�g�l�w���ߩR�A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e���СA�H�����̭n�q�C���w�L��A�w�L�H�ߡF���w���ΡA�w����D�F�����a�D�v���q�A�q�U�ЩҦP�]�C�G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A�D�䨣���Ӥ��_�g�A�����C�u�D�����A�D��u���ӥä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C�H���ĩn�A����۩ު̡A�T�L���סC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ġA�ӱ��W���A�H���_���A�礣�����C�j�D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~�H���A�礣�����ΡA�G�g�l�Q�ۥߤ]�C 6.
�����Ҳ�D����u�ҡA�����ܩ��A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j�����ӽ崼�ܲ��A�Ӥ����D�̡A�H��L�]�C�D��L����(199/260)�]�|���A�D�䤣�L�h���C�G���e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ѩ�崼�A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
�Ҥl��e�z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q�A�ӥ�
(202/260)�Ĥ������@_ (�Ϩ�j���`) �� �l��G�u�Ϩ�j���]�P�I�w���t�H�A�L���Ѥl�A�I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v�q�W���A�l�]�O���C�G�j�w�A���o���A���o��S�A���o��W�A���o��ءC�G�Ѥ��ͪ��A���]����ӿw�j�F�G��̰����A�ɪ��Ф��C�֤�G�y�ż֧g�l�A�˾˥O�w�F�y���y�H�A���S��ѡF�O���R���A�ۤѥӤ��C(��23)�z�G�j�w�̡A�����R�C�v�]�ԫ����`�A�Y�����ĤQ�C��.�^ �i�Ÿt�դl���q�j 1.
���e���СA�����w�C�w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̬����w(203/260)����C�\���]�̡A�|�U���ө��F�q�]�̡A�y�U���ӾA�G���F§�]�̡A���U���Ӥ��w�F���]�̡A��U���ӱo��ҡF�H�]�̡A���U���ӭP��ΡF���w���ҥѥߤ]�C 1.1 ���̤]�̡A�a�G�Ƽw�A�Ӵ���ݡF�]�G����A�ӱ��䥻�C���H���H�ۤ��l�B�H�D����B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]�A�ӥH�����̲j�A�̥�ͩ]�C�Z�H�۲����ͩA�ѧO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̩��H�M���O�q�Ѽw�F�Ѩ䥻�����A�ҧ��]�A�����Ӥw�C�G���w���l�C 1.2 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ۥͩl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O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Y�۰���ڤ]�F���w�A�Y�ۦ���D�]�C�G����̡A���ɬ��l���D�A�Y�ɬ��H��(204/260)�D�]�C�H�D���j�A�����j��͡F�˪̩Ҧۥͤ]�A�p��ҥ͡A�h�ͷU�a�F�n�w�i���A�h�a�D�U���A���礧�ƪ��i���]�C�G�R���h�K���Z�A�槵�h�a�D���F�ۥj�t�H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q�۶@�A�Ӥj�Ϩ�̵ۤ]�C 1.3 ���椧���w�A�D�{���i�ˤ]�C�ˤ������A�D�@���]�A���䧵�A�h�M���m�ҡA�w���H�A�Ҥ����ơA�G�j���̥��य���R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ҦܡA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D�̡A�t�H�]�F�G���椧�ܡA�t�H���w�]�C�Ҥ����R���A�w�����]�F�����t�H�A�D���ܤ]�F�ӬҭP���A�Z�D�j���G�H 1.4 �j�Ϥ����]�A�H�w����˦ӱ`�w�֡A����w�H�t�ѤU�ӬҺ��c�A���w����(205/260)�]�C�H���a�䨭�A�L���Ѥl�F�H�ѤU�^��ˡA�ӫO��v�q�F�Ȩ�l�]�A�H�j��ڡF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]�C�\�w�����A�Ӧ���t�A�H�V�ѤU�A��@�ҴL��D�A���D���ܤ]�C 1.5 �ӵϵS�L���j�A���H�Ѥl�ۻ��\�A���H���v�ѤU�ۻ��w�A���H�t�ۻ��D�A�{�H���ˬ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ܡA�ӯ��|���H�X�G�D�A�D�j�Ϥ��t�A�E��P�]�H�G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۵ϩl�C�H���I�Q�A�D���]�A���I�Q�̤����Ѩ�ˡA�A���ˮ��H�Ω��H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G�Ϥ��t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w�ʩm�A���v���a�A�L�@�D�����ҵۡA����ҥH���j���]�C 1.6 �G�t�H���w�A�Q������L�ɡC������(206/260)���ߡA�H�ܩѤU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̡F�Ѥ@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Ҩ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̡F�H���ˤ��G�A�ӧJ����\�w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̡F�G�J�٬��j���]�C�m�֡n��G�u���䤣���A�ÿ������C�v������]�A�Ϥ��פ]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q���A���䤣�ѥ��]�C�H���ͤ]���ʩ�ѡA���ͩ�ˡF�ѹD�H���A�G�q�Ѫ̩��F�ˮ��H���A�G���˪̶��C���ͥͤj�h�A���i���]�C 1.7 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D�W�����A��H���D�C�H���D�A�ڥG�ʡA�P�ͭѥ͡F�ʲ[�|���w�A�P���Ѫ��C���楻�G�ѩʡA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A�G�Ĵ������A�L���R��ˤ]�C�ˤ��P�l�A�@�߬y�ǡA�b�ͤ���A�Y�����A�ۧ��ܦѡA�����e�Y�j�A�ӯ���(207/260)�ɳq�A�B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k�]�A�Y�䯪�v��P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@���ơA�ì���ӡC�G���v����l�]�A�e��@�m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P�A���x����ƥi���̤]�A�G���ˤ��D�A�q���C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U������A�F���ҥR�A�U����B�A�Y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P�X�]�C�G�ͩ�ѡB�k��a�A�ί��ҴϡA�L�����ҦۡA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M�A��դ����ܤ]�C 1.8 ���L��H�D�A�ӥH�H�X�ѡF��H�����D�A�ӥH���k�H�F�P�H���ѹD�A�ӥH�Ѳv�H�F��q�@�]�A�ҥH�D�ҥͤ����A�Ӫ𤧤]�A�G�ҭ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̭���ҥ͡A�H�D��䥻�]�A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ۡA�q�ɥ��ơA�H�ƨ���A�ӥ�(208/260)���ѡA�D�ԩ��]�C�̡ͪA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̡A�ͤ��k�F�e�̡A�ᤧ���F��̡A�e�����F�Ҥ@��ҳq�]�C�G���̡A�D�W�Ƥ����]�A���Y��v�q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a�ڤ��ˡ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Ӽs����w�A�ϦP�m�̤����l�ˡA��Ǫ̤����_���A�ӫ�ɨ�ͥͤ��D�A�X�G�H���w�]�C�G�H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i���]�A���Ӧ椧�A�i�H�ѤѦa�B�٤ƨ|�C�O�H���e���D�A�w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ۧ��l�]�C 1.9 �j�Ϥ����Ѥl�A�I���|���A�v�q�W���B�l�]�O���̡A���J�ɧ��]�C����J�q�G�����A�G����Ѥ��֡A�o�Ѥ����I�]�C�ѹD�P�H�A�L�ɤ��q�A�w���ҥl�A�L�P�����A�ѩ�@��ҤơB�@�D(209/260)�ҥͤ]�C�G�j�w�̥��o���B���o��S�B���o��W�B���o��ءA�p�ި�]�C�H���w�A�H�Ӷ��ѹD�A�ѤD�H�ֳ��I���A���z���Ҵ`���A�өR�Ƥ��إߤ]�A�G��u�L�w��讐�v�A���w�̱o�]�A�w�����ұo�C�b���w�̡A�T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A�ӤѹD�h���]��w�ӻP���A�G��u�w�̱o�]�v�C�j�Ϥ����A�D�H�D��]�A�Ӭ��Ѥl�F�D�H�D�S�]�A�ӴI���|���F�D�H�D�W�]�A�Ӧ��t�H�F�D�H�D�ؤ]�A�Ӧܴ��[(��24)�F�ҤѤ��һP�]�A��w�ҥl�C�G���L�D�ӵL���o�A���ҿL���ӵL�����]�C 1.10 �e���ܸۤ���A��u���{�Ӥ��A����ӱo�v�A�禹�q�]�C�\��Ҽ{�A�D�����]�ӨF�ҫ�A(210/260)�D���o�]�ӳ��o�F�����L�D�ӱo�C�Ѥ����I�w��]�A��M�F�ҨD���b��S�W�ءA�ӯ�o��S�W�ؤ]�F�G�L�D�C�H��D�䦨�w�աI�D�䧵�աI�٦��h�L�D�o�I�ҨD�b���A�өұo�h�Ω��C�ΥH�ѹD���̡A�Ӥ����ܨ��̤]�F�p�Ϥ��D���]�A����w���A�ҨD�̹F�o�F�Ӽw�]�H�j�A�h�ұo�̥�]�H�s�F�����D�A�ۦܨo�A�G���ݥG�D�]�C 1.11 �ҨD�b�i�o�A�h���D��o�F�ҨD���i�o�A�h�D�礣�o�C���w�b�H�A�D�����o�̡A�G�o���Ӧ��l�A�l�h�ΥG��S�W�بo�C��S�W�ءA�b�H�D�����i�o�̡A�e�D����L�ұo�F�H�L�ұo�A�æ]���D���w�ӥ祢���F��(211/260)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A�ӱo�����M�_�]�A�G��D�����o�A�ӵL�D�̤ϱo���A�ѹD�ҵM�]�C 1.12 �H�e�ۨD��w�A�w���h��S�W���H���A�Z�D�L�D�ӵL���o�H�e���D��w�A�ӱ���S�W�ؤ��D�A�w�J�����A�ѱN��P�H�Z�D���D�ӵL�ұo�G�H�G�D���Q�b�ڤ]�A�ɧ^�ʦӦ��^�w�A�D�����l�ӱo���禳�l�o�C 1.13 �j�Ϥ��ұo�A�Ҧۨ䧵��ӡF�Ѥ����I���w�A���p����ˤ]�C�B�ѹD����H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L�ӵۡC�H�H�Ʀ��ܡA�h�ѹD���`�A�H�өw�@�A�h�ѹD���[�F�H�H���ѡA�ӤѤ��H�A�H�Ѧ��H�A�ӤH�L���F�D���D�̡A������ݡA�����L�]�C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@�c�{�a�F(212/260)�f�ѫh���A�q�ѫh���F�p�T���n�A�pŲ�e��A����ۤ]�C 1.14 �����D�̡A��F���L�F�����w�̡A��P��ۡA�H���ҥH�Q�G�D�w�]�C�ͦ��Q��B�ؤԽa�q�A�L�ީ�R�A�Ӷ����䥿�A���w�R�֤Ѫ̤]�C�פ��ͦN�A�K�תﲻ�F���{�@�¤��~�A�J�ɵL�a����F���i�w���̤]�C�G�w�̱o�]�A�o��H�ӤΩ�ѡA�ɩ�Ʀӳq��R�̤]�C 1.15 �Ѥ����I�A���w�i�e�F�R�����_�A���w�i�^�F���g�l�H�w���ߩR�]�C�w���^�A�ӵL�D�G�~�F���ߩ��áA�ӬL��ѡF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z�i�̪̤]�C�Ѥ����w�A�H�ͪ������]�A�ӵ��̱o���A�c�̭I���A�G���]��ͦӥͤ��A���Ӧ����F(213/260)�����Ҧb�A�P���ӫ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ҫD�A�h�{��a�`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Ф��D�]�C�G��ͦ��̡A�v�w�ҷP���]�F��ͦ��]�A�v���\�]�F�ѫh�]��\�ӥ\���աC�S����D��@�A��\�A�@���o�F�e�L�\�]�A�w��ध�ܫv�H�G�ѹD�b�H�ơC�m�֡n�Ҥ��u�ż֧g�l�v�A�Y�ൽ��H�ơA�H�t�ѩR�̤]�C�Ӥj�Ϥ��H�f���L���Ѥl�A�I���|���A�祿�Ѩ�y�H�y�����O�w�A�Ө��Ѥ��S�R�]�A�G��u�j�w�̥����R�v�C �Ĥ������G_ (�L�~�`) ��
�l��G�u�L�~�̡A�䱩����G�I�H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A�H�Z�����l�F���@���A�l�z���C�v(214/260)�]�ԫ����`�Y�����ĤQ�K���Ĥ@�`�^ �Ĥ������T_�l��G�Z���P���A��F���o�G�I ��
�l��G�u�Z���P���A��F���o�G�I�ҧ��̡A���~�H���ӡA���z�H���ƪ̤]�C�v�]�ԫ����`�Y�����ĤQ�E���Ĥ@�B�G�`�^ �Ĥ������|_�Z���@�j���B���u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. ��
�Z���@�j���B���u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A�Ӧ��ѤU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ѤU����W�A�L���Ѥl�A�I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v�q�W���A�l�]�O���C�]�ԫ����`�Y�����ĤQ�K���ĤG�`�^ �Ĥ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Z�����A�©R�P��. ��
�Z�����A�©R�P���F����B�Z���w�A�l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u�F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Ѥl��§�C��§�]�A�F�G�ѫJ�B�j�ҡA�Τh�B�f�H�G(215/260)�����j�ҡA�l���h�F���H�j�ҡA���H�h�C�����h�A�l���j�ҡF���H�h�A���H�j�ҡC������A�F�G�j�ҡF�T�~����A�F�G�Ѥl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L�Q��@�]�C�]�ԫ����`�Y�����ĤQ�K���ĤT�`.�u���v�r��u�¡v.�^ �i�Ÿt�դl���q�j 1.
�W���Ѥ����I�b�w�A��S�W�ءA���]�w�H�o���A���ϥH�j���Ө��R�]�C�T�N��M�C�L�����]�A�H�ꤧ�w�F�Ӥ����]�A�H���δ����w�F�P�����]�A�H�^�B�j���B���u�B������w�F�һP�ϦP���ѩR�A�ӧJ�ɨ���]�F�өP���۲j�C�P���l���Z�^�A�Х��[¨�A�H���m���F���B(��25)�~���A(216/260)�Ǧܤj���A�H�w�k���A���w�k�ߡF���u�Ӥ��A�Ӥ���H��ܳ(�x����) (��26)���t�A�[��𰤧�w�A�����p�ˡA�L�����e�F�ӵS�Ю��B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A�Ʈ�ӡA���H�ۨסA��S�i�٤]�C�G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ѩR�A��Ǫ��祲�áF�ѹD���x��w�A�U�i�H�o�I�G���j�Ϥ��w�A�ӥ��~�ΩP����Z�F�\��Ҧ��צ��P�j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 1.1 �j�ϧ����ˡA�H�W�v�q�F��B�Z��M�A���@�z�ۻ��A�����N�ӡA�Z�^�B���B���\�F�j���B���u���w�A���]���ӯq�j�F���䬰���~���G���̨o�C�G������A�j�Ϧӫ�A������Z�B�P���j�F������w�ܨo�A�Ө���ѳ��I��p�o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Ѥl�A�䤣(217/260)���]�A�өұo��S�W�ءA�礣���Ѥl�F�B�����̡A�W�ӽ���A�U�����l�F�Х��ǫ�A���ݦܼw�F�ר��L�Ҽ~�o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G�C�H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A�ӰV���L�֡A�D�J�D�D������СF�H�Z�����l�A�өӤ��L��A�D�J�~�z�䨭���ӡF�ҤH�����̡A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A�l�����z�A�@�z�۩ӡA�w�H�q���A�Ӳ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H�v�����~�䯪���A�H�l�����Ǩ�w�~�A���T���w���̤j�̡A�ӥ�o�Ѥ��̥��̡C�H��Ϥ��w�A�Ӥl���J�~��ӡF�H�Ϭꤧ�t�A�Ӥ����J�@��~�A�i�H���o�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Ӥ�����L�~�o�C�ϡB��Ҥ��o�A����W�o���F�ϡB��Ψ���(218/260)�Ѥl�A����D�Z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A�T���b�o�A���i�פѹD���L�̤]�C 1.2 �ѹD�ֵ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D������A�p�ϡB����A�@���Ѥl�A�@�o������l�F�Ũ�ұo�A�U���Ү��F�s��ҷ��A�L�G�P�C�\�ѹD�յ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H��H���w�өw�F�e���a�ӳB�A�h�L���P�o�C�H�Ϥ����x��、l���v�A�D�H�����Ӧܩ�ҡF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A�D������ӡA�ש��B(��27)����C�ѹD����H�A�\��˨�x�٨o�C�G�j�w�̡A�L������F�ҳ��Τ��@�A��o�S��W�ؤ@�]�F�Ѧ��H��(����)�ѹD�A�L���i�x�]�w�C 2.
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o���S���w�A�ӪZ���E�ӤѩR�Ӭ��Ѥl�C(219/260)�H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[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X�w�A�j����ѤU�F����y���j�R�]�C�G�w���ܪ̡A���쥲���A�p�ϡB�Z�O�]�C�ҪZ�������Ѥl�A��Ʋ��ϦӼw�P�F��ɦa���P�G�Ʋ��A��R����H�ƨ�˫h�P�F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פj�]�C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@�j���B���u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w�L�F�@����(��28)�Ӧ��ѤU�A�H�\�Ω���F�\�w�J�ۡA�ѩR�ëp�C�G�L���Ѥl�A�����]�F�I�H�|���A����S�]�F�H���ݦӤ�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�W�]�F�ɦ~�ܤ[�A�ǥN�ܥáA�v�q�W���A�l�]�O���A����ؤ]�F�ҤѹD�Һ֡A�Ӳ����Ѽw�H�P���]�C�Ϥ����P�Z���B�P���A�ᦳ���]�A�ӬҦ���(220/260)���F�i�����ƿ˪̡A�L�����]�C�H�Ϥ������A�Z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Ө䦨�P�A�G�Ѥ����I��P�F���D���h�Φ������A�ۨD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o�C�G�ϡB�Z�ҥH�����w�A�ӬҨ��ѩR�F�����ѹD�����A�N���䦨�w�C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Ӯv�ϡA�����Ӯv�Z�P�F�h�H�Ҧ����A�ӬҦp�ϡB�Z�B�P�����t�o�I�Ѥ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]�C�G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A���D���w�F���w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 3.
�Z���B�P���Ӥ�����w�A�ӯ�ɧ��H����w�A��[�H�h�o�I�\�l���ƿˡA�D�{�ۭP�䧵�A�H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H�v���w�A�H�L�a��ˡA����ˤ��ߡA�H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A�J����(221/260)�ӡF�S���䧵�A�H�q�v�R���A�Ш�\�~�A�ӫ�w�ˤ��F�C�G�䬰���A���W�^�i���ͨ��A�礣�W�L�a���\��F�����D��ӡA�~�Ө�~�A�H�j��w�A�ӳ���\�C�ӯ�W�L�v���A����L�a�F�U������A�\�w���ɡF�ѤU�]�䤯�R�A�k�w���ˡF�l�]�O��W�ҡA�йD��ҩl�F�M�ᬰ�����ܡA�Ӽw���j�̡C 3.1 �Z���B�P���~����Ӫv��[�A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J�~��w�H���䨹�A�_���䤯�H���ѤU�A�ѤU�w�A�A�H�v�P�ǡA�E�L���u�B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§�v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ߪv���C�W�ƥ����H�t�ѡA�ѩR���s�A�èɫp�֡F��l�]�A�ܩ�Q�@�F��ҥH������̡A���b(222/260)�@�����^�i�L�a�A�Ӧb��j��v�B�~��ӡB�z��ơA�H����w�]�C 3.2 �Ҥ�����ͤ]�A�ڪA���A�T���ѤU����G�A�ӵS��諐(��29)��ڸ`�A�Q��F�L��סA��D���ɮ�H���v�]���o�I�Ĥ�����ӡA�n�Ӭ�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�ѤU���L�d�A�H�����p�ˤ��ߡA�Ӳ`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�h����Ҥ�i�~�{�̤]�C�Z���B�P���A�D��H���Ӭ��ӡA���Ƭ��ơA�D�F����ϥ������A�Ӥ��o�w�Ǧ��礧���F�J�L�Q�ѤU���ߡA�G�ѤU�k���A���l�ۦܡC 3.3 �s�z(��30)���|�A�ѫJ�w�ӡA�����ѤU�v�P�A�D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Z�����ӡA���b�@���F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w�ѤU�����A(223/260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F���ҿ��~�ӭz�ƪ̤]�C�Τ������q�A�פ���ڨƮ�ӡA�ӪZ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D�~�ӭz�ƪ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�����ӡA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Ӧۤ��F�M�H����H���e�W�A�L�i�i��(������)�A���D��@�Ϥ��D�F�ѫJ����A�`�h�䤯�A�h����k�̡A�B�T�����G�F��ɤ���a���`��A��L�H�ۦs�F�H�����o��D�A�L�H�o�ϡC�G�蠟�`�A��ۥl���A�D������ӡF�ѤU�v�P�A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A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ơF������ӱϥ��A�ӨƦw�ѤU�A�L�L�ҨD�]�C�Z���籩���ӬO�D�A���ƬO���A��D�D���]�F�H�ϥ����j�ơA��`�����p�`�A���i�P�סC�Z�����p�Ӭ�(224/260)��j�A�D���~�ӭz�ƪ̥G�H 3.4 �G�Z���B�P���۹F���]�C�F�̡A����q�F�L�Ұ��]�F���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Һ��]�C�Z���B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ڮ蠟�p�`�A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ˤ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סA�ӳ�����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F����ҥH���F���A�ӧJ�ٵ��~���z�̤]�C�p��ή蠟��A�a���|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ˡA�H�Ѥl�L�a���F�A����ˤߥH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]�Ч����q�A�w�v�q����A�粽����§�F�H�ɥ����Ѩ䥻�A�Ӷ}�v�D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F�B���]�C 3.5 �[�ҪZ���J�ߡA�@�~�����ɬF�F�w��߳W�A�H�إ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F§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s��(225/260)�A�H�ɦѦѥ������q�F�ҧ���F�̤]�C�P����M�C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A�D�©R�P���C�Ӥ�B�Z���w�A�H���F�СA�s��§�֡A�ϤѤU�L�Ѥ�Z���W�A�Ӭ��h���A�O�P������F�ӵ��~�z�]�C�\���Z���w��A���ɥ��[�A�Хߦӥ��j�ơA�w���ӥ����Q�A�����J�b�R��(��31)�A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ӯP(��32)�A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l�A�H���ҥ����B���ҥ����A�h�ѤU����Y�w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x�t�A�Ӥ���ϥ����ӡA�S�����F�]�C�G�P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A���P�Z���áA�Ө�\�P�w�A�稬������i�Q�̨o�I�G�ҥH�t�H�٤]�C 4.
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§�C§�̡֪A�Ф��Ҧs�A��§�֥H�Ч�(226/260)�A�G���榨��ѤU�F����j���B���u�A�b�`�H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L�]�A�Ӥ����P���R���A�H���ѤU�Ф]�C�G��§�A�F�G�ѫJ�B�j�ҡB�h�f�H�A�L���P�]�C�Ѥl�ܱf�H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欰�H�ͤ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ߡA�L�H�͡F�P���F�G�D�A�G�H§�Ч��]�C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A�b�p�����ҦP�A�b�x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šF�G§��t�O�]���ӥ͡C�Ӥl������A�Y�ˤ��Һa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A�ۦp�x�šF�Ӥl���l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o��F���ɨ䧵��A����ұo��A�Y�˥ͨ������ɪ̡C�H�ѩR���ˡA�Ͽ˳Q��֡F�H�x��L�ˡA�Ͽ˨���a�F���P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A�ӥH�U�ѤU��(227/260)���H�l�]�C�ܳ��H�l�j�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L�Q�⤧���A�ר������椧���ΡC�����ܴL�A�ˮ��ɷ��A�T���H�Q�Ӵ���C�Ѧ����P���Ч����L�N�A��i���P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]�C 4.1 �ҧ��w�q��ѡA�ѩR�ұ¡A�����ѧ��C�h���R�Ӧb��̡A�����ѹD�A�H�ߤH�h�A�G�Ч����i�w�]�C�P���Ӥ�Z���w�A����ˤ��СA�ӧJ����w�A�H����ˡA�H������A�D�F���p�P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ܺɦܩ]�C�G�䧵������ϪZ�A�Ө�H����§�A���ѤU�ӬҦw�A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߫�@���W�A�Y����Ͽ˱ڤ��w�A�礣�h���A�G�J�êZ���Ӻٸt�F�b�ۦڤ���A(228/260)��Ѥl���F�F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~�A�ӱҤl�]���E�W�F�D�ܼw�E��P�G�H�G�P�����w�A�i�צܨo�I�^�L�����]�C �Ĥ�������_ (�K��A��䯪�q�`) ��
�K��A��䯪�q�A����v���F�]��n��A�˨䭹�ɡC����B���§�B����֡C�q��ҴL�A�R��ҿˡF�Ʀ��p�ƥ͡A�Ƥ`�p�Ʀs�F�����ܤ]�C�]�ԫ����`�Y�����ĤQ�E���ĤT�B �Ĥ������C_ ��
�v�q��§�A�ҥH�ǬL�p�]�F����A�ҥH��Q��]�F�ǨơA�ҥH���]�F�ȹS�U���W�A�ҥH�e��]�F�P��A�ҥH�Ǿ��]�C������§�A�ҥH���W�Ҥ]�F�v�q��§�A�ҥH���G(229/260)����]�C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§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A�v���p�ܽѴx�G�C�]�ԫ����`�Y�����ĤQ�E���ĥ|�B�Ĥ��`�^ �i�Ÿt�դl���q�j 1.
�ѧ��ˤ��D�A�H���ˮ��A�h�ˤ��W�A�Ҧ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G�����楲���v���A�ӳ]�v�q�A��u���ɤ�§�v�A�ѬO�_�o�I�j�H�H�ͨ��ҭ��A�D��u���͡v���D�A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P���Ҥ@�ߩҺ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͡A���ͥ��u�q�v�l���v�A�H���䥻�]�C�G���ɤ�§�A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F�͡v�̤]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F�ͬ����D�A�G�̤@�]�C§�]�̡A����D�B�o��w�B����ʡA�G����(230/260)��§���A§���ӧ��q�j�A�H����q�䯪�A�ɨ���]�A�ѷq���ɥ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A��q�@�]�C 1.1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F����ͤ���F�ӥ������H�ۡA§�����ơF�����t�ܥ��w���СA�Ӽs����]�C�G§��ơA�Ӽw�U���B���U�F�F�p��˥H�Ψ�L�A�L����q�A�˦���R�A�q�R�ҦܡA�h���ɤ��D�ߡC�G������§�A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ɥ��䥻�F��§�ӥ��䥻�A�O�i�f���D�C 1.2 �G�p�̫p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˪̷R���A�L�̷q���F��§���j�h�A�ӵ��t�ҥѿ�]�C�ѵ��t����A�H�O����`�A���䳯�]�A����ѻ��F�H�ܨ�p���B����R�q�F��§��ҥѳ�(231/260)�]�C�G§�̩l�שʡA����w�ӥ���D�A���i�ѥ��Ӭ�§�]�C�t�H�R§�A��Х��]�A�H����w�A�j��D�A�өw�䱡�ʤ]�A�G�H§�ӭP�v�j�C 2.
��§����A�ӫ᪾§�Ф����F��§��ΡA�ӫ᪾§�Ф��ġF�~�w�ӿ��A�N�w�Ӧ��v�C�w�Ф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§�H�����C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K���ߩ�§�A��§�H����w�]�A�Ҹt�H�Х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§���N�]�C�O�G���v�q��§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§�F���ฮ��§�A�����ɤ�§�F�����Ѥ�§�A���|�P��§�F���h�j�Ҥ�§�A���m�f����§�F�����~��§�A����y��§�C�U����h�A�өw�䵥�t�B����(232/260)�p���B�ܨ�q�R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ӡB�@�����w�A�ϱ��ʤ��ɡA�_�~�ʮ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A�Ӭۦw�v�A���_�ĩ�D�A�H���ѤU�v�C���t�H§�Ф���N�]�C 2.2 �G���v�q��§�A���䧵�̤��q�A�H�R�ƿˡA�H�q�^�L�A�˴L�����A�Ӳ��ɤD�ơC�ѩv�q���ɡA���q�R���q�A������H�ηq�v���ڤ��D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A���k�k���O�A�w�L�p���t�A�C�Q�⤧���F�|�w�H�Ц�A�|���H�L�ѡA�|��H�U�\�A�e�U�H�s�f�F�Ѧ����ɦөw�@�m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@�ڤ��w�F�Ϫ����k�k�A�U�o��ҡA�H�w�H�v�F���Y�H§���a�̤]�C�ӥѻ��a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A��D�����~�O�C 2.3 �G������§����(233/260)���`�A���䳯�]�A����~�H����ۡA���䤺�H�P��q�A�ϥ��[��»��A�ߨ�§�`�A�ӵۨ�۷q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F��w�A�E��͡A�U�w����A�w�䱡�ʡA�@��ӵL�ζáA�P��w�L���֡A�h�H���ҩ���w�A�ӤѤU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F����§�Ф��Ĥ]�C 2.4 �G§�̡A�ߩ�H�ӹF�A�l��H�Ӳש�ѡF�H�w���D�A�H���k�ʪ̤]�C�H§�P�v�A�b�w�F�H�Ц��w�A�b���U���F�ѧ��H��§�A§�H���w�A������稭�̤]�C�ѧ��H��§�A§�H�w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v�H�̤]�C�G���̡A���v���H����A�۪v�v�����\�A���t���ҥH�l�Ф]�C 2.5 �[�ҩP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§�A������§(234/260)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C§��J���A���w�k�p�A�D�����v�A����x�]�C�\��ߨ���A�H�T�~����A�q��Ѥl�F�v�q��§�A�F��ѤU�A�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ӬҷR��ˡB�q��L�F���ˤ��`�A�Ƥ��p�s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Ƥ��p��C�i�����w�A�p�����U�A�ϮɵL�Ѩ䥻�A�H����͡A���ҧJ�E��͡A�H�w�䨭�A���Q�ƦӪv�A���ݥO���ӱq�B�¤��ӫH�F��o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]�j�I 2.6 �G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§�֤������ơA�v���H�@����ˡB�v�䯪�A�ϬҺɨ�R�q���ۡC�����Ƥ��A��p��ұСA���Ҧ���ܧ��A�ӯ����§�֡B���F�D�w�A�H�֨�ͦӫO��l�]�C�G���L���۪v�A�ӤѤU(235/260)�L�����o�C�O�תv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A��§�Ф��ġA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Z���d(��33)�]�C 2.7 ��§�̡A�d������A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§�A���Ϫ��䥻���A���{�ϥѨ���`�]�C��§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A�����w�F�D�̤]�F�h����m�H���w�F�D�Ӻɨ䧵�A���Ҧ��w�F�D�H�ɩA�ѤU�|�����v�̥G�H�G��G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§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A�v��S�ܽѴx�C�v����Ĥ��ۡB�椧���]�C�H���߭�����§���ҴL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ҿˡF�ӷq�L�R�ˡA�H�����L�ɡF�����R�w�A�H���w�F�D�C���۶i��v�A���ݦb�W�̤��F�O�F���۩���w�A���ݦb�W�̤��D�¡C�G��P�v�w�A�S�����x�]�C 2.8 ���`(236/260)�Ҥ���§�P�v���D�A�D�ܹD�]�C�ܹD����H�ʡA�H�ұo��ʡA�h�ѤU�ү���D�A���W����v�w�w�]�A�G�v�ꥲ�D�䥻�C
�i�v�t���l���q�j_ (���z�Ĥ����j��) 2. ���̤��e���СA���G�D�̤]�F�b�H���D��ͦӲv��ʡA�L����͡B����ʡA�D����D���j�h�C��
�Ҥl��G�u�D�̡A�Ѧa���w�ǡF���̡A�H�����ܼw�C�v�H�D�z�U���ӵL���z�A�G��u�w�ǡv�F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L�����A�G��u�ܼw�v�C���䥻�H���ʡB���H���͡A�ӱo���D�]�C�H����͡A�ʱ��P��F�ʤ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ۡF���h�L�A�۫h���F�H���ӰʡA(240/260)�E�����c�A�c�h���D�C�G�����̤��i�a�A�Ө��~(��35)���y��]�F�H���~�䱡�ӵS�����E��͡A������D�H�R��ʡA�ϩʥD�ӱ��q�C�ʵL�ҷl�A���L�ҼW�A�ӫ�A�M�A����D���j�h�]�C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H�R��ʡC 1.1 �w�̥X��ʡA�ʥR�h�w�ۡA�w���h�ʨ��A�G���w�Y���ʤ]�C�w�̩l�A���l��}���}��A��u�@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D�v�F�~���̵��]�A�����̩ʤ]�C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ҩl�A�Y���Ѥ���A�@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D�]�C����L�ӹD�L�W�A�ۨ�L�ӦW��L�W�굽�F��L�h�}���}��]�C�H�ͬ����A�Ҧ���}���}��A�Y�����Ҩ���~�A�ӹD���i�W��(241/260)�̤]�C�N���}���ӥR���A�פ����F�N���}���ӥR���A�פ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Y�e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A�Ӭҥ��C�H�����L�L����A�{���R����F�R�ˤ��w�A�Y����]�F�G���̡A�H�H�@�����w�A�Ӧۨ�}���}�त�i���̤]�C�G�����ʤ������A�ӤH���ܼw�]�F�G���D���j�A�w�����C�H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�ۧ��l�F�ꤧ���v�A�祲�ѧ����C�G���A�U�椧��A�ӤѤU���j���]�C [���G 1.2 ���e���СA�g�l���D�A�L�D���w�F�D���ơA�Ӧ۸ۥ��ܩ�v���A�Ѹ۩��ܩ��|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ҩl�A�l�Ӥw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Ҧ��A���䧵�Ӥw�C�G���̤H�ͥ��ɤ��D�A�ӸU���@��(242/260)���w�]�C �Ҥl�H���ꤤ�e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w�A�ӿW���䦮�A�H�~�۩����q�A���v���H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w����G�A�T���~�G����]�C 1.3 �Ҩ��D���x�Ѫ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ѥj�A�в����J�Ѹt�F����
�Ҥl�߱Ф���N�A�ӥ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]�C���j�t�H�H�����w�F�D�A�ӱ��v�ΤH�A�ѤU�ҳQ��ƪ̡A�����j�ϡF���h�P����Z�B�P���C���Ƹt�̡A�Ҩ�ܼw�A�Ө�l�A�Ω�ѤU��@�A�v���x�]�C 1.4 �Ϥ��j���]�A�H���x�B��。B�̶ơA�ӵS�J�ӥH���A�ϤƬ����ݡA���o�j�ۡA�ץH�w���ۻD�A�����I�C�����Ѥl�A�I���|���A�H�^�i��ˡA�L�a����A(243/260)�өv�q�W���B�l�]�O���A�H�t�Ѥ���F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̤j�A�Ӽw���ܷ��A�G����Ѥj�R�A�Ʃӫp�֡C�Ѧ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q���A�Ѥ��Ҥ��A���H�䧵���m�ҤH�����ƨ�ˡA�H�ֳܺ��C�Y�H�����ͤ��D�B�ߩR����A���W�g�Ϥ����]�C 1.5 �Ϥ��H���o�Ѥ��d�A���H��w�]�F�L�w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ѹD�]�C����ʡB�R�䵽�A�H����͡A���D�H�X�Ѫ̤]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䦨�ۤѩʡA����}���}��A�ӧ�����Ѥ���A�@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D�]�C�����D�P���p�T�A����ʤD�����T�F���ѤH���۳q�A�Ӻ믫���ҹF�]�C�G���楲�q�����A�p�j���G�I�j���̡A�w���̤j(244/260)�F�j�w�̡A�P����̬L�F�G�j�w�����j�R�A���Ϥ��ҥH���Ѥl�]�C 2. �ҧ��A�ܼw�]�A�Ӥѳ\���A�P�H�ܺ֡F�֦]�w���A���ӫp�֡A�����ܼw�C�ѤH�ҷP�A���̥G�w�A���t�H��q���]�F�R�Ƥ���A���̩�w�A���g�l���ߩR�]�C�Ѧ��ѤѹD�A�F�R�ơA�L���p�T�A�T�D������Ǥ��ơA�ӫe���u�p���e���v���D�A�Y�H���P���C�i���ܸۤ��̡A�����ۭP��w�]�C 2.1 �ѩR����H���o�A�H���M���v�A�����ۨ䤣�ѡA�ӽӬ������F�]�䱡���A�Ӧh�g��S��W�ءA�����P��w�A�ӵL�H�o��S��W�ءA�B���䬰�ͤ��D�F��{(245/260)��צӳh��a�x�A�L�H�۱ϡA�ӬҽӤ��ѩR�A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o�A���i���K�A�Ӽ~�w���ߥͲj�I���\�̼}�䦳�o�A�ӪY��ΧK�F�H���ѩR�L�̡A�i�H���O�D���F�E�Ϲ��Ƥ��ߥ͡A�Ӱ����Լɤ��ߤ���F���Ҥp�H�����A�ӥ��G�ɤ��̤]�C�G���~�w�A�h����ӦӮ���͡F�����ơA�h����w�Ӱf��R�F������H�D�A��H����ѹD�v�H�G�g�l���ɤH�ơA�H���w���ߩR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Ѭ����餧��F�D��ɤѤ����A�i�R����A�ӵL�H�ʨ�ߡA�l��ӡA�G������R�B�N�@��T�A����i���D�]�C�[�G�j�ϥH�����R�A���D���ӳ����u�A���D�֦Ӻ����p(246/260)�F���T�t�H����A��Y�H�D�����C�ҿɤ����w�A�ܸۤ��\�A�ҥѦ��P���̤]�C 3. �u�L�~�v�H�U�U�`�A
�Ҥl�ޤ�Z���w�A�H���j�Ϥ����A�P���ѩR���i�x�]�C������w�ܨo�A �Ҥl���٤��A�Ө�ޤ��A�~�j�Ϫ̡A�h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R�A�B�v�ѤU�]�C�H���w�L��A�w�L�w�H�o���F���w�L��A�w�L�D�H�v���F���w�L���A�w�L�ХH�����C�p�ϡB��Z�B�P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o�A�Ӥ�����СF�����o�A�Ӥ�����v�F�����o�A�Ӥ�����w�F���ҥH�Ҹt�H�]�C������w�b�A�H�����䧵�F���̥H�Ѭ��w�A�n�ͦӷR���C���(247/260)�����ӦӷP�ѡA�o�Ѥ����I�̴�A�G��ר�ӥH����w�C���ѩR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۫p���]�H 3.1 �Ҥ���Ӥj�����ӡA�ӥH���u�o�Ǧ�B����A�O������o�F�Ǩ�l�Z���A�බ��ӡA�~�z��~�A�H���ѤU�A�O����l�o�C���බ�����N�A�@��СF�l��Ӥv���ӡA�z��~�F�Ϥ���@���W�H���w�١A�Z�D�Ѥ��ҫp�̥G�H�G�Ҥl�٬��L�~�]�C 3.2 �ҤH���~�A��̼~�w�����ߡA�䦸�~�~�����ǡA�䦸�~�v�����j�A�䦸�~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U�~�Q�S��դ����o�C����A�t�H�]�A�Ҽ~�b�w�P�~�P�v�A�ӬҹE�ҨD�A�B�D�ҨD�A��o�j�A�G�N��~�G�H�n(248/260)������ҨD��v�H�h�b�u�Я������w�Ӧ����A�Ҥl�]���~�Ӥj���A�}�V�m���v�Ӥ[���A�O�T�̤���ҨD�]�C 3.3 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䦨�A�D�H���v�P���u�A���L�Ӥ]�C����ߩӦ��ӡA�[�H���u�ҧ@�A���D��w���ߡA�H�ٯ��Y�����@�C�G���椯�R�A�s�n�w�~�A�H�i�j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V�A�ڤ�ΧѡF�J�����A�~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A�Ӥ��R�w�P�A����Ӥw�g�A�ӵS���]�C�h�ȰӬ����ɡA�ѤU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o�w��F�@�Ҥ�����A�Y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ɡA�^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h�D�ҥH�ɤ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ӻP�ơA�ҿ~�]�C�H�ɤ����ܡA�������ΫݡF�h���D����l�A�H��(249/260)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~�z�̨o�I�G�ҨD�̡A�J�Х��w��v���A�J���^�~����A�Ӭұo���A���~�v�H�G��L�~�]�C 4. §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H�D�F�H�D�̤��q�]�A���q����u�s���ݬF�v���C�]���ӭ��˿ˡA�]�q�ӭ��L��F�]�˿˴L��ӥ͵����A�h§��_�j�A�M�ҩl�]�C���̨ƿˤ��D�A���H�D�����A�礯�q�����C�G
�Ҥl��§�A���]�F�H����§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H§�v��A�h�ФƬ����F��§�Ф��ҥѥߤ]�C 4.1 §���l�]�A�]�G�Ұ����ۡF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A�Ѧa����]�C�ѧ��H�R§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B�p��(250/260)���w�]�C�G§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@�q�]�C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Ѧa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ǡA�G���ۤ�§�ۡF�����H�v�q��§�A�q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§�A�G������§�ơC�]��D�ӱ����A�ϥ��V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v�w�A�G�»�§�`��§�]�A�ҩҥH����w�A�F��D�A�Ӳ������]�C 4.2 ������§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A�Ψ�P�v���\�F�h��§���T�ʡB�»��T�d�A�ҥ����ҩl�סA�Ӳ��H�G���e���w�]�C�P����§�A�����䧵�A�G�K���䯪�q�B����v���B�]��n��B�˨�ɭ��F����A���§�A����֡A�H�ɨ�R�q�A�䥲�礧�B�����B�]���B�ˤ��A�ӵS���(251/260)��§���֡F�H����ͫe���`�ѡA�Ψ����Ҧw�̡A���Ʀ��p�͡A�Ƥ`�p�s�]�C���̤��i�_�͡A�`�̤��i�_�s�F���l���ߡA���Ԧ����`���A�G���p��ͨ�s�A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ܦ�G�H�G������§�A���ɨ䧵�]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L�ɷ��]�F�D�ˤ��ݡA���o�ܨ�^�i���ۡF�D�椧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p��^�i����C�G������§���p��L���A�ӥ筺��L���]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ۤѤl�ܩ�f�H�A�P�]�F�G������§�A�����f�H�F�Ӳ�����§�A�L�Q��@�]�F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o�C 5. §����A�Ө�\�h����v�A�H§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]�C(252/260)�������ʡA��G�ХH�|��w�F�ХH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˿ˤ��w�F�ХH�q�A�h����L�大�w�F�ХH§�A�h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Z�A�M�R���H���w�C�w���j�A�G���k��A�ϤѤU�Ҧ��䧵�A�h���w��ơF�Ө�Ыh�Ʃ�§�j�C���]�B�q�]�A��`���ۡA��§�۲j�F���]�A��椣�i��A��§��j�F�G�w�Ц�§�Щl�A��§�Y�H���w�]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A�s����w�F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ϴ_��ʡA���Ǥ�§�F�_§�Y�_�ʤ]�A�_�ʧY���H�]�A�G��J�v�_§�����C 5.1 ���A�H�]�F§�A�z�]�A�j�q�P�]�C�_§�̡A�k�B����D�F�ʤ��Ҩ��Y���A�D���ҵۧY§�F�k���h���ʡA�_§�h���D�C�G§�̡A�F�D(253/260)�̤]�F�S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H���Ҽi�A�����ҳB�̤]�C�G§��ơA�ӥ����Ҵ`�F���Ҵ`�h�w�A�w�h�v�o�C��§�H�u�w���v�@�v�]�A�����h�w�v�A�L���h�M�áA�m��§�n�w�����o�C����J�`���ӱ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�ӭP���v�F�h�䬰��ԥB�ơA�H�ۨ�Τ]�F�G§��T�ʡA�T�d�̡A�ۥΪ̤]�C 5.2 ���D�A�Ω�ơF�G§�]�ƦӨ�A�]���өy�F�s�䥻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ΡA�ӫ᪾§�C������§�A���ɧ��]�F��§�R���A�h�Ч��]�C�»���§�A���P�v�w�F��§���ΡA�h�Ъv�w�]�C�G��§�̡A���D�䥻�F��§�̡A���D��\�C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L�סA���P�۪̫v�H�S�Z�ɥ���L�Ѭ�����(254/260)�̫v�H�ҥ祻��D�A����ʡA�ɨ䤯�q�A�F��w�H����͡A�өw��ǦաA�|��ij�̥G�H�G��§����A�@�Ҧw�v�F��§����A�ꥲ�æM�F§����§�A�\�i�Q�o�I 6. �u�v�q��§�v�@�`�A�Y��§����ΡF�]�����ӥܤl�]�A�]�����ӥܤH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b��R�w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R�˷q�L���N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ΡA�h�Ш�R�w�����A�ӬҺɨ�R�˷q�L���ۡC�B�H�^���ӧǬL�p�A����ӿ�Q��A�Ǿ��ӿ��A�ȹS�Ӷe�U�A�P�ѦӧǾ��F�Ҧ]��§�H����СA���ҥH�פ�§�Ф]�C���G���A�ӫ����§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§�����A�ӫ����§���D�F����§���D�A�ӫ�(255/260)��§�Ф��ġA�H§�P�v���\�A�G�Q�G���䥻�]�C�v�q�H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F�䧵�F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W�ҡA������D�F�e���D�o�A�H���Ҵ`�G�D�A�Ӥ�����ʡA�|��ꤧ���v�H�G��G�u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§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A�v��S�ܽѴx�]�I�v�ҭ�����§�A�R�w�𥻡A�q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]�C�H�H�ӤѡA���ѩR�H�̡ͪF�H�w���͡A�ɨ�ʥH���ѡF���פ��D�C 6.1 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A�D���Ҩ��]�F�]�D�H���СA�H�ҳ뤧�Ӧ���w�A�H�ҥ��ͺɩʡA�H���ѩR�A�h��L���w�B�v�o�C�G§�̡A�����w�̤]�F�Ф����w�A�ӥ�§�j�A�H�ܤ��ۡA�өw��ӡF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`�A�Ӳߤ��H���Ǥ]�C�e�v���L�H�A(256/260)�U�w��ҡA�h�L���w�F�U�۪v�䨭�a�A�h�L���v�F��§�v���Ҧ��A�ӥ�����§���j���]�C 7. �B§��_�]�ɡA�Ө�Υ�]�ɡC�j�̥�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�§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j�A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F�D�Q��ʦӷĩ��A�H�۶è��ť���ʡA�E�`�䤯�C���`�h�͵S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͡A�h�ѤU�èo�C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A�N��H�ۦw�w�H�G�H�G��§�H�_���]�C 7.1 §����§�A�H��H�����A�J�H�����A�ˤH����ť���ʤ]�F�`���h�զ���ť�B�ئ��ҵ��B�f���Ҩ��B�⨬���ҰʡA�Ҥ��A��~�A�ӯ�O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G§�̡A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ӥΤ��A����(257/260)��w�աC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�§���J����A�H�d�����M�F�G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|�A���D§�̤]�F�D§���|�A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]�A�ӱ������ҨϤ]�C�G�`§���J�v�A�J�v����_§�F��§�Ф����w�A�Өϥ��Ѥ��i��D�]�C 7.2 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D�@�ݤ]�F�����ҵo�A�D�@�Ƥ]�F��ť���ʩҦܡA�D�@�Ҥ]�F�]�ɦӮ��A�h�Ȥ��_��ʪ̡A�礣�@���F��§�����A�礣�@��`�C�G§���]�ɦӦ��ΡA�D�ɤ��y�A������\�C�M§���H�ɰ_�B�H�ɥΡA��D���@�A�Ө䥻�h�L���A�H�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]�C�H���D�w�A�L�H����͡F§�����w�A�Y�H���H���͡A�Ϥ�D�]�C�G§�Ъ̡A���D��(258/260)�]�A���G�H�D�ӥߪ̤]�A�D�{��䯴�ǡB�w��L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ڡA�H�T�����Ǥ]�F�Y�{�H�����ΡA�E��§�Ф����A�L�b�G�H���ä��o�C�G§�������C
. |
�L�Z���i�t �L�t�Z���� �t�Z�p�N �ּz���� |
|||||||||||||
|
�]��ƨӷ��G�~�I�^
|
||
|
��9_ |
���[�G 1.�b�v�����ߡC�m§�O�P���e�n�G���l��G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G�g�l�A���ѥ��[�A�ϨD�Ѩ䨭�C����
�G�� �`�G���e����A�ϥ֤��[�C�� ���w�� 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B�[�ҳ��W�]�C�@��G���A���]�F�[�A���]�C�j�g�h�i�֫J�Ӵ��[�A���g�i���J�ӳ]���]�C�� 2.���T���ؼСC
�]���s �m�_��Ũ��n�G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ت��a���৹���F��A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A�H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_�M�̡C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 �m���q�Ш|�M¾�~�Ш|�n�G���u�n�b�߲z�W�Ͼ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ت��A�O����Ҧۤv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O�b���ɪ��ӤW�A�n�ϥL�̱楿�[���h�C�� (�t�i�Ѿ\���e���q17-15-14�g��) |
|
|
��10_ |
���۽t�G1.�k���F�k���C�m���P����էd����֡n�G���۽t�s�����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C��
�B�f �`�G���۽t�A���äW���C�� 4.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Y�A���W�p��C�m���v�P���v���@�n�G����C�며���A�@��I���P�m���a���]�۽t�o�x�̡C�� ���Ҫ��G1.���ު����C�m��~�ѡP���Ķǽסn�G���J�Ӳۦ��h���`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A�ץH�֮��ʡA�ު����աA�T���ѯ�J�����A�o�C���m���v�P�I�ǡP�J�ڡn�G���� �B�@ �ɡA�ʦ��Ҫ��̬Ʋ��C�� |
|
|
��11_ |
�m�j��§�O•�p��n[�S�W�G�m�j���O�n, �m�j��§�n] �C�D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w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A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F�A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x�A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ơA���ƥ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ơC�Y�ʦӵL�ơA�w�ӥ����A���`�ӥ����A�w�P�����H�H���䲦�ߤꪾ���A���H����ꪾ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~�פꪾ�~�A�~���ѷN�ꪾ�w�A�w�H�X�F�ꪾ�F�A���q���ꪾ�x�A�x�v���h�ꪾ�ơA�Ƨ٤����ꪾ�ơA��w��֡A�ָq��סC�v(������Ǯѹq�l�ƭp��) |
|
|
��12_ |
���u�G3.�S���F���@�C�m�Q�ѡP���ѧӡn�G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@�A��g�åD�A�����t�j�C�� �� ���Q �m�ճ��}��n�G���b���u�ӥB�M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C��
�M ������ �m���֡n�G�����u��D���A�ҩ��h�F�١C�� |
|
|
��13_ |
�S�G�C�m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]�C�m�}�b��n���H����爲�S�C�m�֡P�j���n廼�q�S³�C�m����n�S�A���J�A���]�C �m�p��•���蠟��•����n�G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B���S�H�^�C�v |
|
|
��14_ |
�F�E�G�V�F�E���C�S��
�P���� �N�ʳ��� ��� �F�E�� ���� �C�m���ǡP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n�G���� �P ���F�E�A �� �G �j�̡C���m��y�P�P�y�W�n�G���T�t�ܡA ���s �Y�A�Q�@�~�A �դ� �D���A �P �D�F�E�C���m�~�ѡP�a�z�ӤU�n�G�� �դ� �� ���� �ұѡA ���� �F�E �ܨ� �C�� |
|
|
��15_ |
�D�W�G 1. �� �ɥH �Ӥ��` 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Ǭ��C�D�i�`�W�d��A�V����@�C��H�٬����D�W���ǡ��A��٧@��
�D�W ���C ���D�l ��|���D�W���C�m���D�l�P�G�`�n�G���H�D�N���T���A�h�f�X�D�W�C���m�v�O�P�Ѥl���D�C�ǡn�G�� �Ӥl ���ǡA���� �� �� �A�ӥD�D�W�C�� |
|
|
��16_ |
�����G�p�p�����B. (�@�@��s���) |
|
|
��17_ |
�߽͡G 2.���ɶ��u�ȡC �~ ���� �m�ѼJ�n�G���ΤC�Q説�Ӥ��J�A�Υ߽ͦӫʫJ�C��
�� �c�ӾF �m�︾���Ѱݡn�G���Υ߽ͥH�ܹ����A�Υխ��ӥ̥���C�� �� ���v�D �m�ػ��^ij�n�֡G���ک��߽Ͷ��A歘�Y�ը����C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
�m��ǻ��ҡn�G�����W�a�ҵۡA���t説�����h�A���T�I�ѵ��ԡA�S�P�t説�����C�ܩ� �� �C説�A���b�߽͡C�� |
|
|
��18_ |
�����G 1. �� �ɪk�a �Ӥ��` �M ���D ���ú١C��@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k�a�C��H�� �� �� ���ǡC�m�v�O�P�����C�ǡn�G���Y���M��i�ׯ��
�� �� ���N�Ӳ� �ӧg ���k�C���m��~�ѡP�ŦO�ǡP�Ծ�n�G���F�Y�r�A�n �� �� �k�A���c���_�C�� �M ���� �m�D��茝�S�¼s�F����ϫo�H�G�Q���n�G���F竝�� �l
�� �A�D���� �� �� �C�� 2.�ɫ��Ūk�C �M
�Ӷ�P �m���ǡn�T�C�G���� �� ���ɪk�A�� �|�] ��ۡA �� ���դ��A�k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Ƥp�A���`�Ƥj����¢説�A����a�I �� �� �A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 |
|
|
��19_ |
Ĭ�i�G 1. �� ���a��a Ĭ�� �B �i�� ���ú١C �~ �Z�T �m�����n�G���Φa���v�A
Ĭ �i ����C�� �e�� �e�� �m������n�֤��T�G���ѥL�s�����\�A Ĭ �i �ק@�h�����C�� ��ҶW �m�ʤ��M���n�ĤG���ĤG�`�G���ӵS�� �s�F ���^�Ҧ��A���� Ĭ �i ���ޡA�����G�]�C�� |
|
|
��20_ |
�]�d�G 1. �K�� �� �]�Z �M �� �� �d�_ ���ú١C�ҥj�N�L�a�C �]�Z ���m�L�k�n�Q�T�g�C
�d�_ ���m�d�l�n�|�Q�K�g�C�m���l�Pij�L�n�G�� �]
�d �Τ��A�L�ĩ�ѤU�C�� ���� �`�G�� �] �A�� �d �� ��[ �N �]�Z �F �d �A�� �Q�Z�J �N �d�_ �]�C�� |
|
|
��21_ |
�m���l•�ɧ��n�u�դl���|��ۡA�¤C��Ӹݤ֥��f�C�v |
|
|
��22_ |
�[��(�[Ů)�G ����F�i�h���o�C�m���P���d�չB�R�ס֡n�G���\��
���椧 �[Ů��e�A�Ӥ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]�C�� �B�} �`�G���[Ů�A�ק���]�C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 �mа�ѡP�����n�G���i�h�[�١A��ƵL�Ҽg�A�D�I���V���A�B�w�I���C�� |
|
|
��23_ |
�m�j��•�ͥ�����•���֡n�i�֤�j �� |
|
|
��24_ |
���[�G �@�ʷ��C�y���m§�O�P��§�W�n�G���ʦ~����B�[�C�� �G�� �`�G�����A�S�n�]�F�[�A�i�]�C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l�n�ɾi�D�Ӥw�C�� �]�ƥ�
���ѡG���ʦ~�̶����B�~�B�B�ʧ@�A�L�Ҥ��ݩ�i�C ���慤 ��G���H�ͥH�ʦ~�����A�G�ʦ~�H���W���C |
|
|
��25_ |
���B�G�j�N �P �ڪ���S�C�Ǭ�
��^ �����]�C�L�E�p ��(�t����) �a(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)�w�~�A���g�ɨ��A�P�O��o�i�A�~�Ͳ��C��ά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C�m�����P�~���p�ݰꨯ�q�f���y���O�n�G���詺����A���|�p���A���Ь٭V�A ���B �����C�� |
|
|
��26_ |
��ܳ�G�m�ѡP���}�W�n�G��ܳ�o���A�@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 ���I ���ǡG��ܳ�A�۹�L�k���סC���o���X��ѩʵM�]�C����]�Ҥ����ѩʬ�����ܳ���C |
|
|
��27_ |
��B�G 1.�� �P��� �� �P�Z�� �C�m�s�l�P�����W�n�G���^�D ��B
���i�Ѫ̡C�� �J�` ���q�G�� ��B �A�Y ��� �]�C �� �R�����ѫJ�����A�o�M����A�G�� ��B �C���m�f��K���P�Q�]�n�G��
�� 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 �P �v�C �Z�� �����C ���� ��G�� ��B �N�H�L�ۧڤ]�C�� �Z�� ��G�����l�ۡA�N�� �� �]�C���� |
|
|
��28_ |
�@����G 1.�פ@��W���ˡC�Τ��A���硨���@����A�פ@�ΧL�ӳ� �� �C�@�A��@�� �� ���C�m�ѡP�Z���n�G���@����A�ѤU�j�w�C�� �� �ǡG����A�A�]�F�@�ۦ��A�ӷ� �� �C���m§�O�P���e�n�G�� �Z�� �@�j �� �B ���u �B 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ѤU�C�� �G�� �`�G�����A�L�]�C��Ū�p��A�n���~�]�A
�� �����n�p��K�K���� �� �̡A���ΧL�� �� �]�C�� �տo�F ���G�� �G ���H�笰 �� �̡A�H�Q�@�~�[�L�_ �s�z �A�Q�T�~�� �� �A�O�A�ۦ��A�A���o�٤@����A�G�H�笰
�� �C����x�٥ΧL�@�Ԭ����@���硨�C |
|
|
��29_ |
諐�G�� �j�P���^���C |
|
|
��30_ |
�s�z�G�j ���e �z��W�C�b��
�e�n�� �s�z�� �F�_�B �s�� ��n�C�۶� �P�Z�� �b�����|�ѫJ�ô� �e �A�G�@�W ���z �C�@�����@ ���z �A��_�@ �s�z �C�����N�L�a���ԭn�a�C |
|
|
��31_ |
�R�֡G��@���R�֡��C ���~�C |
|
|
��32_ |
���@�@�G�~�ӡF��ŧ�C�m�¤��N�v�P��ѡP���Ҭ��W�n�G���e�¹��M�h���A���ԥ蠟�j�\�F�@�@�A�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C���� �k���� �m�^�����n�G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ӫҨ��ѩ��R�A�@�ХA�ϡA���S羣�͡C�� ���ӯP�G�Ѳ��P�\�~�C
�� �k���� �m���y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{���|�D�n�G���۩��Ҥ��߷����ΡA����@�p�A�p �� ����h�A �� �����l�A ��
�Z ���ӯP�A��l�]��q�Ӥ��C�� |
|
|
��33_ |
�� �d�G�P���� �P �P�d��
���ú١C�v�٨�ɤѤU�w��A�D�����ΡA�G�ΥH�٦ܪv���@�C�m�֡P�P�|�P���v�n�G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 �d �A�W�ҬO�ӡC���m�~�ѡP���Ҭ��١n�G�� �P �� �� �d �A �~ �� �� �� �A���o�C�� |
|
|
��34_ |
�y�K�۽g11. |
|
|
��35_ |
���~�G���A���]�A�Ω����F�~�A����]�A�Ω���~�C�ޥӬ����ƩM�T���C�m�֡P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֧ǡn�G��
�� �H�c �|�٤� �L�z�A���ਾ�~ ���� �A�Ϧܲ]�áA���G��w�j�C��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