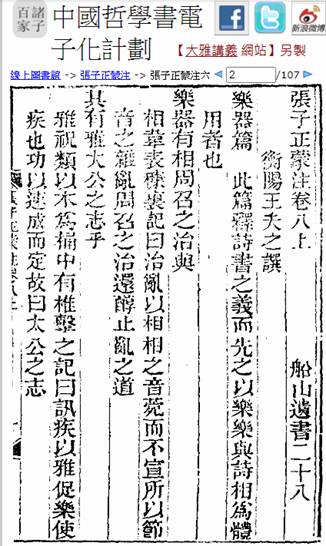�m�i�l���X�`�n_ (wts)
|
�־��g |
08FF-15 |
�j�����q ���}_ http://www.jackwts.tw/ |
|
�j �D �� �� |
�� �� �� �� |
|||
|
|
�m�־��g�n[�t���G�u�W�Ϯ��] -> �i�l���X�` -> �i�l���X�`�]�P�v��s��ѥ��^��8-9] ���g���m�֡n�m�ѡn���q�C�ӥ����H�m�֡n�A�m�֡n�P�m�֡n�۬���Ϊ̤]�C�־����ۡA�P�B�l���v�P�I�ۡA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C�m�O�n��u�v�åH���v�A�ۤ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šA�ҥH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áA�P�B�l���v�پJ���ä��D�C�䦳���A�Ӥ����ӥG�I���A�M���A�H�쬰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C�m�O�n��u�T�e�H���v�A�P�֨ϯe�]�A�\�H�t���өw�A�G��u�Ӥ����ӡv�C(3/107) ���̥��]�A���v�Ӧ楿�]�A�G�T�e�мF���A�Ӥ����ƨ��I�q�����A�q�ӱ��A���v�ӥ��H�A�H��L�D�A�Ƥ��o�w�C�m�֡n�禳�m���n�A�祿���Ӫ��q���A�L��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��m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\�w�A�ܡm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G�פ��m���n�A�P�־������P�q�C�Y���H���m�֡n�m�֡n���z�@�C ���m�H�Z�n�A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ѤU�A�H����Z�\���R�A�q�m���M�n�H�����C(�۪`�G�����R��) �`����R�A������Z�\�C�m�j�Z�n�A�Z���S�A�����H�Z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R�A�q�m�Z�n�H�����C(�۪`�G�a�̻R��)
�u�A�P���S�A�����H�Z�\�����ѩP���A�i������v(4/107) �q���q�]�C(�۪`�G�Q�T�R�j.)�u�u�v�A�m§�O�n�@�u�c�v�C�����m�֡n�m�֡n���X�@�H�H�\�C�Ǫ̾ǡm�֡n�h�Ǽ��A���P���A�l�צP����z�C���俳�o�ӷ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j�~�A�h���R��i�A�H畼��|��A�o��Ʒ~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C [畼(������)�G����F�i����}���j��爲�q畼��畼] 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A�[�H���ӡA�s�ӫ�L���A��Ӥ�§�q�A�J�i�ƿ��A�X�i�Ƨg�C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A�|�䭫�̤]�C�ĵo���ӳq�ѤU���ӡA�s�ӭs�A��Ӹ`�A�ɤv�P�H���D�A�ɩ�O�o�C�����Ƨg�H���A�i�H���L�A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A�ѤU�L�D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`�A�G���i�H���ǡC ���Ӧܸ֦��A���H���i�W�A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A�G§��ܲj�C(5/107) �H�A�ߦ��䦨�Ƥ��H�]�C§�A����ƦӦ��k�h�]�C�֥H���F���A§�H��ƦW�A�G�Ǹ֥i�H�����A�i�H����C �����٤Ѧa���D�A�D�t�H�ӯ�v�I�Z����z�ӥ����A�ݤH�ө����̡A�ҫդ]�C�t�H���Ƥ������A�s�G�ܦX���ƥi��A�G��U�Ѧa�Ӳר�ΡC�֤H�סu�Z�^��¨�A���ۤ��D�v�A�٨|���@�ݤ]�C�ѯ�ͤ��A�a�ন���A�ӷr�u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̡A�H����]�C¨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D�ӥ��ɬL�ۡA�Z�^�]�Ѥ���A�ɦa���Q�A�H�H��X�Ӧ����A�Z�t�H�ҥH�ΤѦa�����Ӥƨ�w������A�ϥR������A�ҭY���C(6/107) ��§�B��D���A�Τ�ν�A�~�����Ӥ��i�`�]�C��A���]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q���H��A�����l�h�s���H��C�����]�A���w���ӨƥB���A�D�]�ɦ]�Ʀӷl�q���A�b���Ƥ���A�B�����]�C���U�B�䰾�A�G���i�`�C�L�H�~�����A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F�����~�Ƭ��A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C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A§�]�l�q���H�P���A�L�@�w�����b�~�褧���]�C�����]�~�`�����D�s�G§�A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i����§�H�����C�U��uø�ƫ���v�A���ר���A�r���P�Ӹq�I�U���A�G�]�⤧(7/107) �u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ø�H�C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¥�ø�H�����Cø�D����A�h�夣���H�šA�G§�H�H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A�u���Ƥ����ӷl���l�B�ɤ����]�C(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`�q�A��N�i�l���N�ӳq��) [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m�A�f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)���k��C�o�O�ò����]�褸�e757-�e735�~�b��^�����ҤH�A�O������v�W�ۦW���зǬ��k�C�o�٬O����j�N�Ĥ@��k�֤H�A�m�ָg�n�����m�P�P�n�B�m���n�B�m�f��n�B�m���n�B�m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֡A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 〇�u�F���x��v�A�W�U�L�`�A�D�����]�A�i�w�~�A���ήɤ]�C�u�b�ҥ��k�v�A�ҿױ��ήɪ��P�I�@�Ӧ����A�W�]�A�F�]�F�h�Ӧ۬١A�U�]�A���]�F�@�F�@���A�Ҧ��Ѳ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x�A�h���R�L���Ӥ@�D�C�����@�A�h�s�ٷU�Y�A�F���@�ߡA�w�~�@�P�A���°��i���B�s���ɩʤ��K�ΡA�@�t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ܨo�C 〇�m���b�n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ӱ���B�A�G�L��F�ޥ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8/107) ���B�A�G���H��僃(�P��)�ơC�����A�Q�⤧���A�B�A�p�ߤ]�C���w����⤧���ӧѤv�p�A���B��L�Q�ӫ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p�H����e���A���o�B��B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]�C���ۮ��A�o�w�s���N�A�D�צ��y�Ө��S�]�q�C�ۮ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g��o�o�C�[�����w�A�H�p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A�Өp�߶����A�h�[��ź�F���h�p�H�s�e�A�ӫ��Ӥ��H�Q���A���D�]�A�ڹD�]�A�U�ǻ��ӡA�K���H�s�z���l�\�]�C 〇���V�աAij�s���A�k�l�ҥH�^�����B�p�g�˪̨��o�F�S��(9/107) �u�Ϧڤ����A���ΨD��f�x�A���u�B������ߡA�Z�O�L�P�I���ަ���m�ǡn�����Ӽs�����C�ɤ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H�R����x�A���u�B������w�]�F�Z𡚱�H���Ӥ��A�h���B�[�X�w�o�C [�V(������)�G�i����j�¤]�C �V�աA��W�C�i�֡P�P�n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աC�i���j�V�դ]�C] [�P���u�]�e12�@���X�H�^�A�V�m�A�P��A�W���A�ѩ�O�֤l�A�S�W�u���A�O�P�Ӥ����ĤT�l�A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ͤ�] 〇�m�̴šn���ϥ����ԥh(�W�n)�A����ϥ����ԶˡA���ϥ����߷q�Ӥ��p���H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P�q����A��q���w�C�D��敎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v�I����敎�A�G���n�@�C 〇�u�����v�A�U�ϫj�]�F�u�k�v�k�v�v�A�Ǩ䱡�]�C(10/107) ���U�g�l�椽�ӫ����k�A�o�G���A��G§�q�C ���u���աv�A���ڤU�p�ҫh��p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C�j�ҫh��j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C�ƫh�����W�N���C���H�হ�A�h���G�p�֮`�F���ߡA����L�]�C�@�h�����C [����(���� �|����)�G�j�N�s���C��椭圆�ΩΤ�ΡA�騬�Υ|���A���y�M鋬�C盖�@�릨带��兽头�ΡC����_�ӥN�M��P�e���C�Z��x���s���C] 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p�v�v�A�h���X�a�L�l�A�����v�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a�H���ľv�ӧ@�X�A�j���X���S�v�A�����l�A�h����¶(11/107) 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Ӫ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Ӥ�����e�]�C [�X(������)�G�j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C �o���B�v�g�C] ���m�d���n�m�ŵءn�u���A�B���v�A���קg���v�ūp�A�h�U���o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Ӭ��W�i�O�]�C�B�A�ש~���w�]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A�ҥѧ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Ҥ��ߡF�g���ک��A�L�Үe�䶡�o�C ���m�ӹ|�n�u�U���m���A���]���N�v�A�����Ҩ��U�H�U���]�]�C���̡A�l�]���ߡA�M�����M�~�סA�ѤH�E���A�ӫ�§���F�ӧ���i���A�h�b���Ҥ����U�]�C�j�̥H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֡C(�����G�ަ���P�u�F���x���A�b�ҥ��k�v���N�۳q.) (12/107) ���u�k���q�q�v�A�S�̤����A���P����A���Ѹۤ]�C�k�A�Ḱ�F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F��Ӹ��p���]�C���t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q�q���ͷN�b���A���S�̤��n�@���Ѹ��A�D�{�|���C [�q�q(������)�G�O�~�y��J�A����wěi wěi�A�����v�A�����ج����ˤl�A�X�ۡm�ָg�P�p���P�`�Сn] ���m���d�n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h�L�M�A�����h�D�ұo�A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ҸաA�p���ܤ]�C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]�F�L�M�A�L���]�F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F�D�ұo�A����ұo����D�C�A���դ]�A���h�L�A�A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鮦�A�߫�ۥ��A�D�䥻�ߡF�����H�H���Ӥ����D�Ѥ��A�ण�]�H�����A�A�h�n�c�q�ߦӶˮ`�̦h�o�C(13/107) ��²�A���]�A�L�����]�A�ƫh�����j�C���A�h�n�C�L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���K�S�A�D���H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Ʋj�C�դl���e�O�����A�K�H�h�h���C���D�x�D�H�h�G�A�ӿ��@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A�K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ƨo�C�u²��²���v�A����ɧg���ΡA�M���h�̤���L��²���աA�G�֤H����e�⤧���A���s���j�A�����H�d�Ƥ��C�P�ҧg�l�ѩХѱΡB���y����Z�̲��o�C�g�l�����A�w���۱o�A�L�e�@���N�A�G�L�d�j�C (14/107) [�����G�K��ɾ|��D�ޯb�����p�O�C�m�s�l�D�U���U�n:"���դ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Шo�C"�����`:"�����A�b�����O�]�A�D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̤]�C"��ΥH���p�O] ���u�}�ک�v�A�u�ʧ����v�A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áA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{�}���ک����Ӥw�F�|��G�ӡB�a�B�ޡB���C�P�����Ӧw���A�R�H���ܤ]�C�̨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L�P�Q�A����M���w���A�P�����ߡA�¥G���R�C ���m��_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[§��P���A���H�H���]�C�}�v�ӫ���U���C��ר��m�ѡn�u���p�l��s�f�v�C�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֤��ӡC(15/107) [�t���G�t�i�Ѿ\_17���e���q17-14-13�F����] ���E�g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j��§�R�A�h�j�H�i�P�]�C�g�ڦX�w�h§�R�۶��A�j�H�H�D�P�A�ҿסu�P�n�����A�P��ۨD�v�]�C [�g�G����C�i����P�s���r�j�����]�C�i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j緵�˿פ��E�g�C�E�g�A�����]�C�i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C�i�֡P�ǭ��j�E�g�����C�i�ǡj�E�g�A緵�ˡA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] ���m�T�[�n�A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A���P�H�ߩ�M���]�C�e�H�B�ܦӤ����۵��H§�A�����h��`�����H�۶S�l�ӧK�w�A�Y���l���O�w�C�t�H�F��}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s��j�`�A�R���Ӫ��۷P�A�ߵL�p�֡A�h���ڤ���Ѷ��C�H�ߤ��M���A���ߤ��M���Ƥ��]�C ���m�j�Сn�u�����Q�d�v�A�@�����ФE�U�a�C�E�U�a�A�ʤ��]�C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|�����l�A�l�a(16/107) ��K���A�ǥ[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Q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U�K�d���ʯa�A�����u�E�U�a�v���ԡC�����Q�d�a�A�E�@���k�]�C ���Z�^���͡A���b��Ϥ����~�A����F�Ө��^�н[¨�A�w�j�K�o�A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~�v�A���ԡC�ӡm�֡n���u�W�Ҥ���v�A�æb��ɰ����l�]���G����A�Ӹ֤H�٫Һ��C���פW�Ҭ��Ѥl���١A���̡A���w����C��h�^�\�Ҽ����l�A�ͩ�ѫJ�o���B��Y�줧��C���A��S�]�A�S�o�̥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A�A���o�١u�G����v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C(17/107) ���m��Сn�A�K�����K�A�H�`�}���A���ԡC����@���@���A�Q�~�̰ͪ��A���X�̤ϡC���k���B�A�]�o���駡���C���A��ޡB�����D�A�ϡA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ڰZ����S�̤��R�A�H�v�y�X�q�A�D�b���̺��C��ô�̮a�ꤧ�j�C��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u��Сv���u�ŴСv�A�S���u����@�v�A�\�~�C���@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@�A���v���ӥ[���A(18/107) �שP���W���@���C�H�����`�s�ӥh���C�~�`�X�W�u�i�P�@�ǡv���@���A�H���Ϥ��Ϭ����g�X�v����A�ӱi�l�]���A�q�h�����C�i�l���ǥD���߱o�A���վǸԻ����\�h��²���A�Y�����O�]�C ����X�ӳ����ۦ�A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A�B���Ԥ]�A��۪F�Ӧ�A�L�B�ۦ�ӪF�A�P��a�|�X�A�����M�h�B�C����ä��o§���]�F���ﳱ�A�k�U�k�A�H�R�G�`�]�C����o�ӳ�����F�A(19/107) ��w�h�ӳ��v����A��L�|�����ߡA���j�b�H���A�B�פ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ä����D���]�C�u���E�_��A�R�¨�B�v�A���өM�]�F�u�a���b�F�A�h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i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l�i��(�O)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L�B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A�H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A�D�����i�]�C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C [�a��(�x���� �x����)�G�i��别�W�C�ɫ�桥�C���~�a横��] ���b��Ӥl�M�A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I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b�ﳽ���A���n�D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P�I(20/107) �b����n�D��ѡA������Φb�Z�A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i���]�C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ӷV�����A�D�H�o�N�C����P�Ӹq���A�m���n�H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q�A�m�֡n�H�ܴc������ĵ�C ���u����᭷�A�{���_�L�v�A�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S�ɱo�h���̲`�L�Ӥ�]�C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C [�(����)] 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ۡn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m�A�i�o�v�C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`�ʤ]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A���P�A�i���h�A���w���h���i���]�C���w�h�h���H���C ���u�g�l�ҶQ�G�D�̤T�v�A�S�u���ѤU���T���j�v�A���]�A�ʤ]�A��(21/107) �]�C�g�l�ҶQ�G�D�A�D�����Ӥw�F���B��B���ҥ��Ѩ����D�A�ߨ䥻�Ӥ��M�P�A�D�i�H��§�@�֡C�YŪ�Ƥ峹�]�A�ߤ��̯��٤��A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ơA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i�]�C�G�D�H�ϸg���j�C ���e�y�w���A�h���۩M�ӻ�i�P�F�G�ﳾ�D�A�ҥH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]�C�u�ۡv�A���@�u��v. �Ѧa�H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@�]�C���M�h�ѩM���z�A�ѩM�h���Ĩ�M�A�w�I�����A�M��F��U���A�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o�C ���Eå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H�͡A�����ѧ��A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22/107) å�A�Ƥ]�F�E�Ƭ��Ҥ��{�����j�k�C����̡A�D�Ѥ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D�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̦Ӥ��۬��q�A�S�H���ͩҸ�A�p�ͧQ�ΡA�ݦ����̡A�G���W�B���U�B�����B�q���B�[¨�Τ����A�ҴN�H�Ҹ�Ϊ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A�Ѳ����~�H�i���A�ӵ��Τ��̧g�D�]�F���ơA�ѩR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A�ӵ��Τ��̧g�w�]�F�Ҥ��G���ƦӨ��A�G���d�A��å�C�~�H�ᾧ�̤���A���N�Ʈa���A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A�Ҥ�����m�x�d�n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R�P�R���y�A�]�t���|�H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i�l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ͤ����H�P�����A��o�C�g�ѤU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A�G�����ơF(23/107) ���v�ӫ�i���H�A��κɩ��A�ҥH���v�C�v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o�Ӫv�A�G���K�F�F�K�F�H�`�Ť����ӥ����`���C�F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A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X��ѤD����H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A�G���جӷ��F���ثh�H�ɥH�B���C�D�j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v�A�G���T�w�F��X�����A�U�A��y�A�v�]�C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G���]���F(23/107)�`�`�Ӧ�A�H�ѩw�h�i���ݤR�b�A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A�ӫ�M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C�i�x�M����M�A�G���f�x�F�R�b���ӤѶH��C�����x�A�M��i�����Ӫv�A�G�E�H�Q�U�ײj�C�D��X�ѫh�j�k��A���D�{��k�]�C�����Ƥ��A�G�ӷ��B���F�v�L���ӦX�q���]�A�G�T�w�B���C���Ԥ����A��z���@�ݡC�H�����Ҥ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ɵM�̡AŪ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]�C ���u�˿˴L�L�v�C(25/107) �P�D�]�C�S���u�˿˴L��v�C�P���v�|���D�C�q���U�I�A�M�ӿ����h�L��L�A�L���h�˨��ˬ��i�o�C�˴L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̨��o�C�Y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i�H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˪̤����C�L�p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]�C�Y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ˤ����A���v�ӫ���C�姡�h�H�˲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˽�����B�Ϥ��D�A(26/107) �˽�A�˦ӽ��̡C�M�h�ˤ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C���o�A�椧�]�F�ץ��|�ӴL���C����T�w��E�ڦӤE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A��]�F���ӴL���A�h�H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C���T�w��ʩm�ӸU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l�F�E������J�|�ӫ��|�f�h�C�ʩm�A�צʩx��کm���C�o����H���ԤE�ڡB�f���y�l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D�F�f���A�f�h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i���A�קY���H�λ��C�h�E���j�q���H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M�ỷ�̥i���Ԧ��ΡC(27/107) �P�D�H�˿ˬ����A�@��B�Ϥ��D�]�C�m�j�ǡn�סu�J���T�w�v���۩���w�A���Y�դ����`�U ���q���A�w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Ӥw�F�ȧK��c�Ӥ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C�T���A�T�w�����]�C�T�A�j�]�F�w�j�h�ҬI��j�C�x��h�Ǫ��L�q���A�m�Ҧۦn�̡A�i�Ϧw�Ӥ��i�Ϧb�x�C�v昬�h�T���ηL�C���p���ӱ�j�w�A昬�D���ҥH�a���U�]�F���t�@����(28/107) �L�m��A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ΡA�h�����H��w�C �������ֻy�A�q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]�C�ֻy�A�Һq������C ���u�R���ߦN�v�A���R�x�N�e�A���M�ݤH�ߡA���äD�R�A�L�ëh�_�C�z������ӬG�����աA�{�üw�Ӥw�C�u�ӧӵL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P�v�C�G�L�ҥΤR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̡A�t�b���q�C�թ��L�G�z�C�G�����R�b�A���ߨ�N�H�p���]�C�Ѥw�M�ӱ��o�N�e�A�����H�֦ۧӤw�C(29/107) ���l�֥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R�b���ҥѧ@�]�C�l���A�Ƥ��L�]�C�ƫD�`�ӹL��`�ơA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h�[�A�G�R�b�H�M���C�Y�N�����ƾA�p��z�A�h���H���ѤU�Ӥ���A�Хդb�Ӥ��סA��R�b�����I�R�b�̡A�ҥH�f�b�v�����[�A�ӫD���N���]�C . |
|
||
|
�i̹�`���Ʀ����ƬG�έ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S���e�ҿ״c��大���]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z��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ت��h�����n�h�M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Z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Ѷǿ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q�����R�O�]��]�h��W�����ҿi̹�O�]��Ϋh���q�P§�ҿ��n�q�O����̹�O�]�Ѩ��i̹����쨥̹���̥H���ηi��̹���A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꿤�@���ө|̹�j��§�꿤�@�k�ө|̹�h̹�]�_�@���@�k���F�䲳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S�깪��֤��g�C�M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n���o���M�䲳�n���g�j�ְO��|�u̹����W���ֲ��o�ҫݥH�@�̦b̹��U���ֲ��o�ҫݥH�@�̦b���\��W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H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h���~���v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h���l�~�h�g�ڤH���j�ۤ]�Ӽֹ�q�ӦX�M�����ר��ήa�����ѤU�ҥH���j�֤��o�] |
|
���y̹�z�B�y�ۡz�B�y���|�z�T�ةҿת��j�־� �@�B�y̹�z���O�@�Ӱʵ��A�̦��X�۩�m�|�ѡE�q�^�n�F�y����̹�ۡz�A�n�����I�m�Ѷ��ǡn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̹�z�O�j�ӳ̨θ����A�y̹�z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V�����q�C �Ӭ��b�����P�e�B�����X�{���m�ָg�n�ΤW�z���m�|�ѡn�̡A���O�S��̹�r�A�N�O�Y�Ϧp�m�|�ѡn�̡A���y̹�z�r�A��O���l�N�q���ʵ��A���p�y�����z�Ӥw�C ��F�F�P��ɥN�A���O�m���l�E§�סn�G�y�T�~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Ϥ]�A�M�q���q�A�@�ۦӤT���]�A���@���A�|̹�J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V�]�A�@�]�z�A�m���l�E�ֽסn�G�y���M�B̹��B٪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z�B�y�n�֤��H�G���j�R�A���ι�A�k�G��A�����M�A�F�Եo�r�A�����γաA����}�A�^���n�A�q�M�ɡA�R�N�ѹD�ݡC���� �G�B�v�W�èS���y�ۡz���o�ؼ־� �G���ϦӦb�`�m§�O•�ְO�n���y�v�åH���z�@�y���A�N��y�ۡz�����F�־��W�G�y�ۧY̹�]�A��H�`�֡A̹�̥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ˤ��H�R�A�R�@�W�ۡA�]�H���W�j�C�z��O�^�H�i�H���@���סA�N�O�b�F�~���G�Ȫ����ӮɥN�A���@�ؼ־��y̹�z�A�p�F�~���m�ժ�q�n���m�|�Ѥj�ǡn���h��:�y̹�A���ˤ��H穅�C�z�]�O�~�N���y̹�z�A�䤤�y�ˤ��H穅�z���t�@�ҡA���O�èS���y�ۡz�o�ؼ־��A���O�G�ȭn�`�ѡy�v�åH�ۡz���y�ɡA�ߤ����D�[�{�w�N�O�y�áz�n�Τ@�ظ`���־��ӡy�v�z�A��O��y�ۡz�r�Τ@�ӪF�~���骺�`���־����y̹�z�Ӥ���A�ӥL�ۤw�b�ܻy�̤]�z�S�X�H��s���y̹�z���@�V���־��ӳ�@�ӥL�ҥ����Ӥ����A�Ӥߤ��{�����O�@�ءm§�O�E�ְO�n�̪��y�ۡz�����־��W�ɮ��Ӥ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j�C��O���A�F�~�S���y�ۡz���@�V���־��s�b�L�A�ӷ���Ҧs�b�L���O�s���y̹�z���־��C��O�i���A�ܿ�b�m�P§�n�X�{�ɡA�ӡy̹�z�o�ؼ־��N����s�F�C�F�~���~���G�Ȫ��D�o�ؼ־��A�ӥB�˦ۥi�H�y�g�X���ؼ־������۬O�y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ˤ��H�R�A�R�@�W�ۡA�]�H���W�j�z�C�]�N�O�A�b�F�~����A�ҿת��y�ۡz�O���y�R�z�Ӥw�A�D�־��W�C �b�𥽧������m�q��E�֥|�n�̡A�N���X�G�y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ꤧ�H�R�A�����H�`�֤]�C�z�Ө�F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{�m���m�q�ҡE�֦ҤE�n�C���־��J�U���A�S�{����F���ª��_�P�ɡA���@�y�ꤧ�H�R�z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]�`���־��^�ꬰ�y̹�z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ӥB��W�٧�١y����z���־��ɡA���X�G�y�m�j�P���֡n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ꤧ�H�R�A�����H�`�֤]�C�Z�i̹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C�i̹�H�@�֡A�ҥH�o���n�Ӥw�A���D�Τ��H�`�֤]�C���礧��A��h�j���o�C�z�����־��y̹�z����γ~�A�ä��O���`���־����ΡA�ӻ{���ҿת����ָ̥��y̹�z�A�D���ΡC �Ѧ��i���A�v�W�ڥ��N�S���ҿת��y�ۡz���־��A���O�l�@�M�̪F�~���G�ȡA���m§�O�E�ְO�n�̪��y�ۡz�ɡA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r�y�X���r�ѡA��O�N�y�r��F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ꭵ�־ǬɤΤ�Ǭɤ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ǬɡA�]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~�X�{�F���l���m���۽g�n�A�Ҧ���@����s�̡A�q�M�N���c���p�H�ӡA����y���ۡz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ۤ�ǡA�ӥΡy�ۡz�o�ظ`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O�A�p�P��@���u���C�ӳy���dzN���~�C�]���A�v�W�õL�y�ۡz�o�@�ؼ־��s�b�A�G���y���ۡ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ۤ�ǡA�N�ëD���v�u�ۡA���I�A�^�H�Ѥw���M��Q�סC �T�B�õL�y���|�z���@�־���s����H�e ���L�A�G�Ȧb�`�m�P§�n�t�@�B���m�P§•�K�x•�Ʈv�n�G�y�Ʈv�x�ϡB���B�ơB��B�B���B���B�ޡB���|�B���B���A�H��裓�֡z���q��r�ɡA�L�ۤw�S���ݪk�A�ӤޥΤF�G�����ݪk�A�ӫ��X�G�y�G�q�A���A���|�H�ˡA�j���B���o�A���C�ءF�u�̤@�B�G�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髤�e�C�H���v�a�C�z���m�P§�n�̤S�X�{�F�@�ө��饼�����s�s�־��W�y���|�z�ɡA�L�ۤw�]�d���M���A��O���F�G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Ѫ��y���|�H�ˡA�j���B���o�A���C�ءF�u�̤@�B�G�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髤�e�C�H���v�a�z�Ӹ����m�P§�n�S�X�{�F�@�Ө�F�~���٨S���ݨ��L���־��C����ڤW�A�̾ڪF�~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W�E���־��n�̡A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z�Ρy�|�z�����G�y�K�A��]�A�|�A���]�C�H�K�v�a���`�]�z�A���S��ŧ�۾G���Τ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`�m�P§•�K�x•�Ʈv�n���`��C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ҩ��F�~�꦳���־��A���ΤD���m�P§�n���y���|�z���@�־��W�C�]���P�ˤ@�U�A�Ǫ̩ΦҨ��X���ɥN�ܦ�~�~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m���W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A�b�m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֡n�̡A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m�P§�n���y���|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 �^�H�����b�F�~�����٨S���o�ؼ־��A�O�]���p�G�u���o�ؼ־��A�վǪ��G�ȡA�Y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ܤ��٬ݹL�A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Ӥ����ۧڴN�Ҩ����ꪫ�Ӹ����O�A�Ӥ@�w�n��Ӥ����O�_�u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A�i���p�G�G�ȳ��S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|�A�P�L�P�ɬO�F�~�ɪ��Ǫ̾G���S��|���L���s�b��m�P§�n�̪��s�y���־��W���ꪫ�O�C���O�G�Ȥ��N�b�`�m§�O•�ְO�n�]��@�Ҹɪ��m�v�O�E�֮ѡn��P�^���y�v�åH���A�T�e�H���z�@�y���A�N��y�ۡz�Ρy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־��W�A�Ӥ����ΧO�H���ܡG�y�ۧY̹�]�A��H�`�֡A̹�̥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ˤ��H�R�A�R�@�W�ۡA�]�H���W�j�C����־��W�]�A���p���J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z �𥽧����m�q��n�C�J���|�A�ӤG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S�ޥӤ��G�y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A�L���A�|�H�y�a�p��S�A��פ��u�y���v�C�ۡA�U�]�A�H�`�֤]�C���ױ秵���v�F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S���`�C�m�F���ޡn�����|�A��N�]���C�z�ӫ��X�b�m�F���ޡn�̤~�ΤW�F�y���|�z�A�ӥB���X�A�ۦ��H��A�y��N�]���z�A��O�ۦ��_�A��H�ھھ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䪺���|�A�u���s�y�X�F�ꪫ�X�ӡA���O�A�����𥽧����g�m�q��n�ɡA���X�t�_�C�ӥB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־��S���y�y���z���١A�]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ɥi�H���ͤ�y���\�ΡA�ҥH�y�y���z���O���]���Ӱ_�C�䤤���y�ۡz�����O�y�U�]�z�A�Y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U���q�C ���O�A�p�G�h�d�n�����Z�šm�֩��ֶ��E���C�Q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q��Q���n�ޫn�³��N�F�����K�y�m�j���ֿ��n��G�v���۪S���A�X���~�秵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v�F�����A��Q�G�̡C�y���n�A�H�p�����`�A�v�̤U�S�H�M���C��@�צ��n���m�F�����n�C�m�ʤӱd�a�O�n��G���֮a�m�F�����n�A�O����C�m���•�֧ӡn��:�m�F���ޡn�����|�C�z�@�ݤ��U�A�Y���ҿת������m�q��n�Τ�ۡm�q��n���m��ѡE�֧ӡn���m�F���ޡn�����|�A�@�d���N���m�j���ֿ��n�A�Y���ڥ��N�S�����@�ҿת��y���|�z�Ω�m�F���ޡn�]�F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ΨӸ`�֪��O�y�H�p�����`�z�C��O�ۡm�P§�n�����r�y���־��W�H�ӡA���@�ڤۼ־��A�O�u�X���@�ǥ��Ҫ��h�j�ҵ��U�~�X�{���־��A���O�S���@�ӥX�B�A���ݵ�L�۹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m�q��n���𥽤��ɡA�~�u���X�{���־��v�y�X���@�־��X�ӡA���@�ٺ٬��y�y���z���A�ӳQ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F�U�ӡC�ӥB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{�m���m�q�ҡE�֦ҤQ�G�n�C���־��J�����A�Y�A�ϥΦb���֤��C �|�B�p�� �ѥH�W�Q�סA�o�{��F�b���v�W�A���־Ǫ̡A���ެO�_�W��p�p�e�զp�G�ȩ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ä����ܡA��`�����A�Y�p�P��ǤW���w�h�Ωw�z�A�A�����}�A�䤤�X�{�ܦh�����Φk�ۥ��A�f���L�̪��߽צb���A�p�G���@�@�ҹ��A���ӴN�ΡA�Ǥ��X���X�ơC�H�y̹�z���־��X�{���C�Ρy�ۡz���@�Q�G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ͪ���L����A�ӱq���X�{�L���־��A�Ρy���|�z���X�{��𥽥H�e�A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ҽa����ҥH�P�~���]�ѡA�Φ��ҿפT�إj�־����s�b�P�_�Φ�ɥH��~�X�{���Ҳ��C (�����刘���ڡG��国�j�N��乐�v�륿(�Ҷ�)(2019)) �X�Ӧ�Huuhang Luu�o�G��B���ڪ��F�s (https://vocus.cc/article/667cd330fd89780001d74508) |